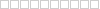舞蹈的表演规范
古往今来,关于艺术的理论很多,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圆满合理地解释一切艺术现象。同样,在众多关于舞蹈艺术的表演规范中,也没有哪一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舞蹈不仅是想象的艺术,更是情绪和形体的艺术,它究竟是理性的还是情感的,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一直没有定论。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对舞蹈艺术进行了研究,指出舞蹈是表现情感的,并首先对情感一词做出了内涵丰富的定义:情感是一个人的内心生活,“是他对世界生活形式的内在感受”,舞蹈再现了“我们内心生活的统一性”,因此是“主观生活的对象化”。苏珊·朗格的解说可谓精到,但舞蹈演员在感受生活的时候,“理性”处于什么地位?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开始解决具体的表演规范问题。
舞蹈表演的特征在于,它永远信任人体,以人体作为唯一的传达媒介,同时舞蹈又借助实在的人体去表达无形的、莫可名状的情绪和心情。苏珊·朗格说:“艺术形象所表现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实际情感,而是他所知道的人类的情感。”情感和本能的宣泄只是舞蹈表演的最低层次,表现自我的气质和个性是第二层次,舞蹈的最高层次是表现全人类的情感,在那个瞬间,舞蹈者脱离了小我而成为大我,代表整个人类叩问世界。
中国在艺术领域很早就超越了模仿和再现阶段,而强调表现性艺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境界说,它虽然一开始着重于诗词绘画艺术,但是对于舞蹈艺术也是有指导意义的。中国舞蹈在许多方面接近于中国诗歌、绘画和书法,表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司空图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造景”与“写境”也同样适用于舞蹈。
从艺术特性看,中国舞蹈和其他传统艺术一样抒情性很强,舞蹈被称为律动的诗篇和流动的绘画,非常讲究表达的美感、结构的精巧和语言的练达。舞蹈是在有限的时空内表达无限的意蕴,因此特别需要创造意境来扩展内涵,增强艺术感染力。此外,中国舞蹈和诗书画一样讲究线条,要求虚拟性和抽象性,也就是用简练的语言来传达人的内心气质,唤起观赏者的艺术想象,最后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情景交融。
和雕塑与绘画相比,舞蹈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舞台形象,不可能长时间供观众把玩,因此特别需要在有限的时空内凝聚情感,用形象传达无尽的情思,所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调动欣赏者的创造性想象,引发他们无尽的思索与回味。因此,中国舞蹈的表演规范可以大致概括为:以情起舞、以舞传情,动而合度、形变神真,技艺结合、引人入胜,境生象外、意韵长存这四个要点(这四个要点具体参见隆荫培等编著的《人体律动的诗篇——舞蹈》一书)。
舞蹈首先是为了表情达意,《诗经·大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舞蹈是人类感情表达的最高形式,形体动作最能抒发生命的激情与活力。难怪诗人闻一多这样说:“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强烈的抒情性使得舞蹈艺术魅力四射:或如短诗,或如画卷,将人类内心的情绪、抽象的思索化为动态的形象。
舞蹈演员固然不能冷若冰霜,无动于衷,但情绪过于外露也并不一定成为优秀的演员。为一己的悲欢离合,或一跳三尺高,或以泪洗面,或仰天长叹,这些个人化的情感绝不能带来优秀的舞蹈作品。真正的艺术家,要像邓肯和戴爱莲那样,要深入细致地把握生活,接受人民的召唤,这样才能超越一己之悲欢离合而成为时代的象征。内心的激情化作外在的“象”,不仅要具体可感,更要有生活气息。例如:张平的《鸣凤之死》不仅有饱满的情感,有鸣凤对于封建礼教的血泪控诉,更有徐徐展开、亦真亦幻的舞蹈之象。高超的舞蹈技巧本来就是与丰富的内心情感相互补充的,正是情与舞的统一,引起了观众的共鸣,从而完成了艺术传达的任务。
舞蹈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本来就是复杂的,演员需要做的不是逼真地再现生活的原貌,而是从生活中提炼出动作,来表达内心的感情波澜和性格特征,这样演员就必须在真实与虚幻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要“动而合度”,动作是舞蹈的基本单位,不动就不是舞蹈。舞蹈动作形式多样,有大小、方圆、高低、长短、曲直、正斜之别,也有刚柔、粗细、强弱、轻重之分,更有进退、动静、聚散等不同姿态。这些动作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现实的一面,但更有艺术的超越性。舞蹈演出不是拍电影或电视剧,演员不需要如实地临摹生活、战斗和劳动的每个细节,例如表现战争的场面,不需要真的拿起机关枪冲锋陷阵;表现收麦子,不需要拿起镰刀亦步亦趋。舞蹈动作和戏曲动作一样,都是通过象征来完成的。
动作合度,自然形变神真,脱离了模仿阶段而引起审美的喜悦。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丝路花雨》中,人们不会计较英娘“反弹琵琶伎乐天”的动作是否准确,而是陶醉在那种婀娜多姿的舞步中去。在《喜悦》中,崔美善干脆把手鼓当成簸箕,但观众完全陶醉在她营造的丰收喜悦状态中,甚至忘记了这一细节。高明的舞蹈演员,不囿于形似,却能达到形神兼备,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
舞蹈动作的技巧往往是高超的,舞蹈家勤学苦练,通过高难度技术动作来博得观众的赞叹。《蝶恋花》中嫦娥和王昭君所舞的长绸竟然有三丈多,充分体现了演员精湛的技艺,更营造了漫天飞舞的艺术场景。《花鼓舞》中演员以各种姿态,从各个角度用长长的鼓穗敲击腰间小鼓。在《长夜行》中扮演盲人艺术家阿炳的沈益民,连续三次“跪滑半角尖挑肩挺立”,最后又用了“空中前扑板腰躺地”。《醉鼓》中黄豆豆或“乌龙绞柱”,或“点地翻身”,或“横空飞燕”,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些精彩的动作都是集中在一张八仙桌上展开的。舞蹈演员身轻如燕,体如游龙,满足了观众的审美要求。可以说,高超成熟的技巧是舞蹈表演的物质基础。
然而,舞蹈不是杂技,它虽然也重视“难”,但更强调“美”。舞蹈演员的表演不同于杂技团里的走钢丝,不是为了简单地满足观众的视觉期待,给他们看没有看过的东西,而是立足于生活,创造美的艺术形象。因此,技艺结合方能引人入胜,舞蹈表演更要注重风格、韵律、节奏等似乎虚无缥缈的东西,虽然这些技巧不像闪转腾挪那样引人入胜,一笑一颦之间,却已然显出功力。
通过上述解说,我们自然就可以归结到“境生象外,意韵长存”这一点上了。舞蹈追求象外之象,摆脱“体物”、“取象”的阶段而要“思与境谐”,在境界上用力,达到物我和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舞蹈的象是有限的,并且转瞬即逝,然而情感丰富,形神兼备的形象,却会“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有限的象,最终能生出无限的境界,传达连绵不绝的情感。从吴晓邦的经典之作《饥火》开始,中国舞蹈演员就开始营造出调动观众想象力的意境来追求艺术的顶峰。中央芭蕾舞团1982年在北京首演的《林黛玉》第四幕堪称中国芭蕾舞创作的经典段落。林黛玉病中的幻觉被一系列亦真亦幻的“幻象”三人舞诠释出来,衬托了林黛玉的悲凉情感和命运,其情其景都有强烈的感染力。
虽然芭蕾和现代舞早早传入中国,但中国舞蹈的精魂却在于这个“神”字,正是“神”要求表演者以形带神,形神兼备,既重视动作上的规范,如迂回曲折、动静求圆、反向起法等等;又强调内心意念的控制,要求表演者身心投入,表达丰富的想象和体验。可以说,癫狂与秩序的合一,是中国舞蹈表演的奥秘所在。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