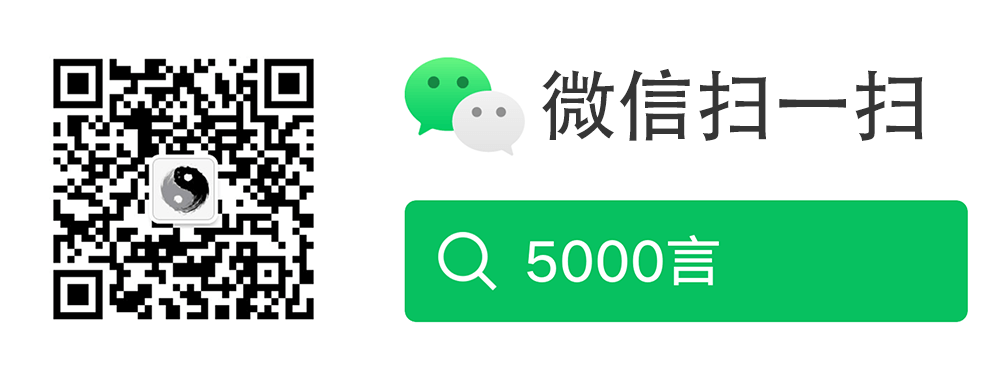人
本文所属分类:孔子思想
对于孔子思想体系中所谓“人”的概念,学者有多种解释。有人把《论语》中的“人”和“民”进行比较、考证,认为“人”、“民”,是指春秋时期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第一》)。其中的“人”,是指上层社会的人物。在孔子思想中,“人”的主要意义是泛指,不是指特定阶级。也有人从“人”的广义的概念上衍生出具体意义。如“女得人焉耳乎”(《论语·雍也篇第六》)和孔子称管仲为“人也”(《论语·宪问篇第十四》)中的“人”是指人才;“不患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篇第一》)和“人皆有兄弟,我独无”(《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中的“人”是指他人,与“己”或“我”相对;“孰谓鄙人之子知礼乎”(《论语·八佾篇第三》)中的“人”置于地名之后,表示某地的大夫;等等。
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人”的观念逐渐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思想家虽然还不能直接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已被明确地放在人的附属地位。如郑国巫者裨灶预言郑国将遭火灾,要挟郑人把镶,子产斥责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虽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但“少也贱”,“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篇第九》),做过小吏,社会生活的接触面比较广阔,在社会动荡、激变的大变革时期,他了解到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和实际情况;加之“好古,敏以求之”,他学习历史,对照现实,分析问题,认识到社会动荡、激变的危机主要来自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他以前瞻性的眼光,要求对于人事、对于人的价值要有所重视,提出“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礼记·祭义》)的理论。这在我国思想认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时代的进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庄子·齐物论》里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论语·述而篇第七》也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就说明孔子对于天、命、鬼、神、怪等“六合之外”的事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的。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第十一》)《论语·述而篇第七》载:孔子病重,子路请求祈祷。孔子便怀疑地问是否有这回事。子路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引用祈祷文说“祷尔于上下神祇”。孔子便揶揄子路说:“丘之祷久矣。”即我早已祈祷过了,可我的病却毫无起色。言外之意就是根本不相信上下神祇的存在。这种对于人事以外的鬼神所持的不可知或怀疑的态度,说明了孔子对于人,对于人事的重视。对于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人殉、人祭制度,孔子也深恶痛绝,坚决反对。孟子曾引孔子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反映了孔子在当时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认识。孔子不仅看到了人的价值,而且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有一些独到见解,深化了他对于人的认识。如“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篇第一》);“节用而爱人”(同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篇第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第十二》);等等。从孔子这些论述中可知,他确立“仁”的概念,是以“人”为前提的。
孔子还按人的道德品质的高低把人分为圣人、善人、成人、君子和小人等。圣人是指具有超凡智识,又能为人类谋福利的杰出人物,“圣人耐(能够)以天下属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篇》)。善人是能本着仁道的原则,消除残暴祸害人民的统治者,“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篇第十三》)。成人即今天所谓的完人,《论语·宪问篇第十四》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聪明),公绰之不欲(不贪得),卞庄子之勇(勇武),冉求之艺(多才多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长处穷困)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可以看出,孔子所谓成人分古、今两种,古之成人是最理想的,今之成人是次之的。君子和小人这两个概念,在孔子言论中经常是对比出现的。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第四》);“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同前);“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篇第十四》);“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罕篇第九》);“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篇第七》);等等。上述所罗列的“君子”和“小人”的种种思想言行,是以道德品质的高下作为评判的标准的。
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的研究与实践考察,在统治者不把人作为人看的情况下,孔子重视到了人的价值。他的仁爱思想,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要求发展人的独立人格,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