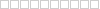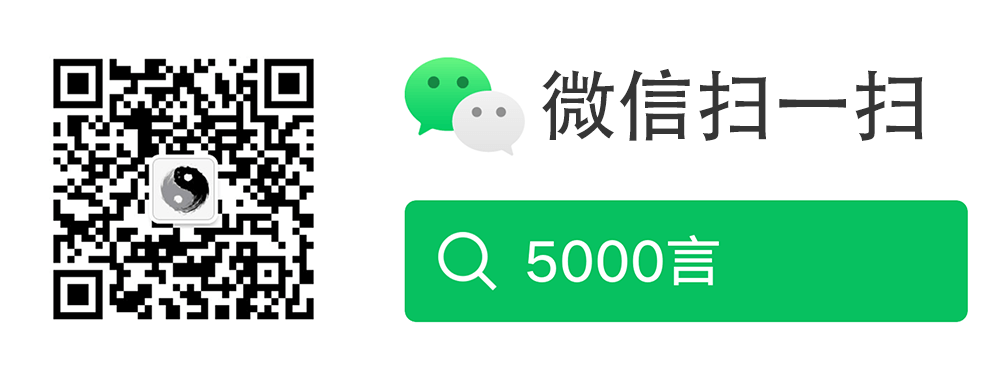东坡词
苏轼(字子瞻,眉山人。生于公元一〇三六年,卒于公元一一〇一年),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照耀今古,与韩昌黎媲美;他的诗,虽不必能赶上盛唐,然在有宋一代,总算蔚然大家,几无后来者;至于词,这似乎是东坡的末技了。东坡并不以词名;后人研究东坡文学的,也只研究研究他的诗文,既经认为末技的词,并没有人去怎样注意。然而老实说吧,东坡在诗歌上的成就,还远不如他的词的成就大些。他的诗,在诗史上不算最好的作家;而他的词,则占在词史的特殊位置。与其我们说东坡是诗人,不如说是词人。在这一点,《艺苑卮言》上面的话已经先获我心了。
东坡的词,后人批评的论调很不一致。而因为词派上的分正统与别派的观念,对于苏词遂发生种种不正确的批评。《四库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轼而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调;然谓之不工则不可。”这种批评,仅说到苏词系“别调”,并没有如何攻击苏词。若俞文豹所说,“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红牙拍板,唱大江东去”,则讥其词不如柳耆卿。蔡伯世云:“子瞻辞胜乎情……辞请相称者唯少游而已”,又讥其词不如秦淮海。至于陈无巳云:“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太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这更显然拿词派来排斥苏词了。可是虽则尽力排斥苏词,实际上却已经承认苏词是“谓不工则不可”“极天下之工”,可见这种种评论,都是为词派的观念所囿着。我们现在既否认传统的狭义的什么正统词派的存在,那末,这样的批评却也不攻自破了。对于苏词还有一种误解。李易安《词论》云:“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世人多以“不协音律”为苏词病。实在,苏词诚如晁无咎所言:“居士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陆放翁更说得好:“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这么看来,我们不但不能责苏词“不协音律”,反而应该称道他能为完成文学的内容,而割爱音律。
辨明了对于苏词的两种谬解,往下更要谈到苏轼在词史上的建设事业。那末,我们不得不承认苏词的伟大了。
在苏轼以前的词,只讲究艳靡,词以婉约为宗,描写是很狭义的,局面毫无发展,故有“词为艳科”之目。到了苏轼才首先打破“词为艳科”之名,扩张词的狭义描写,扩充词的局面,他的词体不限于婉约艳靡,很豪放恣肆有排宕之势;他的词的内容,不拘于“闺怨”“离恨”之情,而抒写壮烈的怀抱;他的描写不只在炼些优美的婉约的词句,而以“诗句”入词,以“赋句”入词,甚至以“文句”入词。这种种改革,总而言之,是词体的大解放。我们即不必论苏词本位的价值如何,单说“词体之得解放”,一方面讲,苏轼为词坛新辟无限的殖民地,得以自由去发展开辟,其革新之功,已昭然煊赫于词史上了,胡致堂评苏词云:“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这是一个很忠实的批评。
王阮亭说:“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实在的,东坡词气象宏阔,我们不应该以读旧词的眼光,来读苏词,应该换一付“壮观”的眼目,来欣赏苏词。他的词除“大江东去”和“明月几时有”二首引在上文外,现从东坡词里面选抄几首词在下面:
凭空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念奴娇·中秋》)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满庭芳》)
这首《满庭芳》词,可说是东坡生活态度之自白。像这种排宕的长词,大都是东坡自己的“怀抱”的抒写。其写缠绵依恋之情的长词,在苏氏集中殊不多觏。但因此而说东坡不能作情语,这就大错了。张叔夏说:“东坡词清丽舒徐处,高出人表,周秦诸人所不能到。”周保绪说:“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且看他的词: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意千里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贺新郎》)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何其?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洞仙歌》)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似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
谁说东坡不能作情语呢?王士祯说:“‘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引见下《蝶恋花》)以上是东坡的长词。东坡的小词,也有很好的。楼敬思说:“东坡老人,故自灵气仙才,所作小词,冲口而出,无穷清新。不独寓以诗人句法,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也。”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在那边,眉眼盈盈处。才是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卜算子》)
琵琶绝艺,年纪都来十二。拟弄么弦,未解将心指下传。主人嗔小,欲向春风先醉倒。已属君家,且更从容等待他。(《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西江月》)
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持杯更复劝花枝,且愿花枝长在莫离披。持杯月下花前醉,休问荣枯事。此欢能有几人知?对酒逢花不饮待何时?(《虞美人》)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蝶恋花》)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道字娇讹苦未成,未应春阁梦多情。朝来何事绿鬟倾?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困人天气近清明。(《浣溪沙》)
这种小词,《词筌》谓:“如此风调,令十六七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统言之,东坡的词,有极豪爽的,有极温婉的。因为他的才气大,所以在长词里面,说来说去,奔踪放肆,越剥越过里,越翻越奇特,句有尽而意不穷。这一半是东坡天才的独到处,一半也因为东坡有丰满的生活,作描写的背景。东坡足迹所至:他生于四川,长游京都,而儋州、黄州、惠州、定州、徐州、密州、杭州……都是他曾经踯躅之所。有东坡这样变迁不拘的生活,产生的文学,也自然是活跃的。至拿东坡的小词和长词比较,则因东坡才气发扬的缘故,长词更适宜于他尽量的描写,小词往往不能束缚他,所谓“曲子中缚不住者”。末了,我且引陆放翁一段苏词的读后感,以作结束:
“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