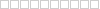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譬”的类推论辩方法
“譬”即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它是按照两种不同事物、现象在“类”属性或“类”事理上具有某种同一性或相似性,以“假物取譬”、引喻察类的过程,通过论说者的由“所然”进到“未然”的认知形式,描述、说明、论证或反驳一种思想的是非曲直。这种方法的特质是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之上的,古人称之为“譬”。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早在西周时代“譬”就已开始运用,《易经》就以“取象比类”开了先河。《尚书》也有运用“譬”的事例,如《尚书·梓材》连用种地、建房、作器三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理做比喻,说明创业和守成的关系;《尚书·胤征》还以“玉石俱焚”比喻说明了官吏的过错“烈于猛火”。在我国最早的一部用文字记载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譬”的思维技巧更是比比皆是,并成为《诗经》赋、比、兴的三大艺术形式之一:“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汉]郑玄:《毛诗正义》);“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宋]朱熹:《诗集传》);比、兴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兴中许多发端起兴之辞多含有比喻义。所以,后人往往将比、兴合称,“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文心雕龙·比兴》),倾诉诗人的情怀。
至以后,孔子以“能近取譬”使这种方法有了定名,“无譬则不能言”的惠施更以“夫说者,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给这种思维方法下了定义。而墨子、孟子、庄子、韩非等人在使用类推方法以论证自己的主张时,更是广譬博喻,充分利用了日常生活中的浅显道理与治国、治世中的深刻道理在某一属性或事理中的同一性或相似性,从而在由此及彼的推论中,成为类推论辩的好手。例如,墨子以类推论辩成功地“止楚攻宋”,孟子以类推论辩使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庄子则以“涸辙之鲋”的类推论辩揭穿了监河侯的丑恶嘴脸,等等。
由于类推论辩方法的关注点只是在于两个思维对象,或用来做“比”的事物与所要论证的事物之间有“举相似”的同一性,从而断定对于它们的思维取舍也即肯定或否定也应该相同。因此,类推方法的特点是:两类事物在某一性质上具有相似性或相同性;将抽象的思想形象化或具体化,是论辩的工具;在论辩的过程中,所要说明的事理对听者来说可能是还未清晰了解的认识,但对论辩者来说,则是已经清晰了解的认识。所以在论辩的过程中,论辩者只是用类推方法或通俗化地或形象化地阐述了一个抽象的道理,并未增加任何新的知识;使表达思想、进行说服说理具有形象性、生动性。它的结论性质是对已知事物的事理之正误的说明,其结论是“应该如此”的价值命题,具有道义性。显然,类推论辩方法依据“类”事理上“同情”、“同理”的同一性,可以增强“说明”的力度,对于古人论辩各种政治伦理问题时“取辩于一物”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表明了现世应该怎样做和为什么这样做的伦理精神,从而以这种思维方法最好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理想诉求,熔铸了那个时代求真的态度与精神,以及求善、求治的振世精神和人文关怀。为此,现代文学家钱钟书还曾就“譬”的强调或联想了两类极不相同的事物之间的相同、相似之处评价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即愈新异,效果愈高。中国古人论譬,说不能‘以弹喻弹’,又说‘凡喻必以非类’,正是这个道理。”(钱钟书:《读“拉奥孔”》,《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也正是由于“譬”是一种言浅显喻深远的思维方法,所以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在谈说论辩中广泛运用的方法,并使之具有了中国的特色。这样的例子从古到今举不胜举,例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是运用“譬”的一篇极好的范文。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