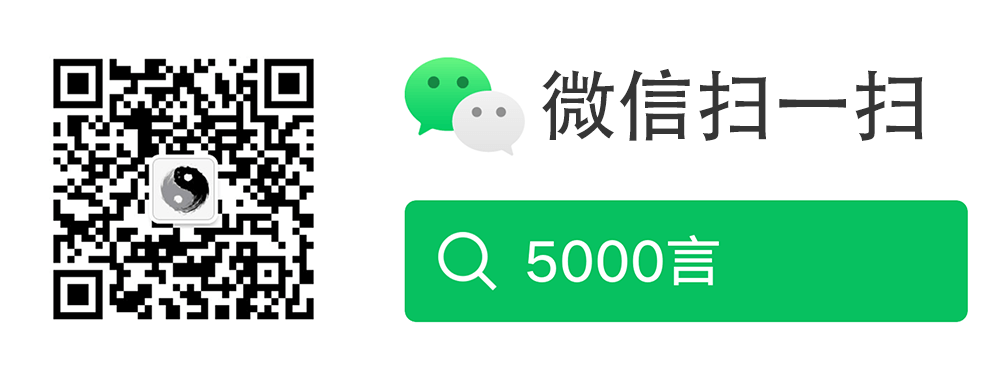《论语》的笔记-论先秦儒家与道家文艺思想的互补关系
作者:sissi
先秦儒家与道家文艺思想的互补关系,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思考。
纵观我们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意识形态上最为活跃、最为开拓创新的“先秦”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真可谓“百家蜂起,诸子争鸣”。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竞相争荣斗艳的百花纷纷凋零的时期,“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下,诸子百家学说自然而然地被压制而衰落,但是,不处于正统地位(个别历史时期除外)的道家,却始终没有被消灭,而是长久的与儒家共存了下来。究其原因,无外乎它们之间有着互补的关系。下面主要从它们的各方面的对立中找相通从而转化为互补。
文艺价值取向方面
儒家更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道家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儒家偏向提倡积极入世,推崇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关注文艺对社会的价值;道家崇尚出世,追求个人的超然独立,更关注文艺对个人的价值。简单来说,儒家是以现实的政治为“家”,道家是以自然的理想为“家”。
表面上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进取,一个退避;儒家思想强调的是艺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思想,道家强调的人与外界对象超功利、没有作为的关系——即审美关系;儒家对文艺的影响主要在主题内容方面,而道家对艺术的影响则更多的是在创作规律方面。但实际二者相互互补、相互制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核心。比如先秦儒家主张文人积极入世,但有时候现实终究会不如人意,连汲汲以求,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子都说过:“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微子篇》)当中国的文人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救赎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产生困惑,从而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这时先秦道家的超世主义特别是庄子的“逍遥游”思想就成了中国文人精神的最后的皈依。林语堂先生也说过,中国文人的社会理想是儒家的,个人理想是道家的。真是深刻精辟的论断。
因此说对于中国文学,由于儒道对文艺不同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文学可以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避免走向任何一个极端。儒家批判社会现实,所以中国文学不会沦于无病呻吟,丧失历史洞察力和改造现实的力量。道家关注人的内心,注重文艺的审美价值,所以中国文学不至于彻底沦为政治的传声筒,丧失超越和批判现实的力量。儒道文艺思想在文艺价值取向方面的互补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可谓是举足轻重。
文艺审美风格方面
儒家主张中和之美,追求“善”与“美的统一”;道家崇尚自然朴素,追求“真”与“美”的统一。儒家向往的是社会美学,注意发挥文艺规范社会秩序的社会功能,道家向往的是自然美学和生命美学,注重文艺对人类自身提升的作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在重视文艺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文艺的审美特性,这种对政教功能的片面性无疑强烈束缚了文艺。它在重视对人与社会的作用,以及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的同时,提出了文学存在的最大价值是因为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因为可以“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因为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儒家的文艺观中,文学的功能是远远重于其本质的,它的价值就体现它具有讽柬功能。至于文学本身是什么样的,并不是儒家的文学观所关心的。
而道家则从根本上否定文艺,但其审美态度、艺术眼光和自由精神,及其对“道”独特的阐述方式,却特别契合于文艺。在道家的文艺观里,文学“美”的这一面就相对突现了,而善的一面,即伦理社会所要求的那种善就淡化了,道家的文艺观所重视的善是对个人灵魂的影响程度,是对个人生活和心灵的指导作用,多是关于对文学创作经验的阐述和研究,这一点,在《诗品》中体现地非常明显。这里,儒道文艺的相对照之下,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儒家的文艺观对文学的外在的教化作用的一味追求,容易忽略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美,导致在政治的阴影下存在,作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而存在,但是这样的一味传道的文学是死的,没有生命的,是僵化的,是无法超越而得到更新的价值的。而道家的文艺观正好弥补了儒家一味重视文学教化性的缺陷,它把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引向了文学本质的方向,一个一直为儒家的文艺观所忽略的方面,在对文学创作的探讨研究中,文学才有条件获得新的生命,才能让各种思想在其中竞相开放而呈现气象万千的局面。儒道文艺观恰成互补,深远影响了后世文学文论。
文艺批评标准方面
儒家主张“思无邪”,道家主张“法天贵真”。儒家认为文学观照的对象,感情的抒发要受到礼乐的制约,追求“怨诽而不乱,好色而不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能过度;道家则要求按照自然之道,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表达要自然率真,不失本色。
儒家在进行礼乐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对于诗,孔子才会有“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训导;对于乐和舞,孔子才会有“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之类的感受。孔子诗学批评上倡导的雅正观,体现了他的“中庸”哲学思想和重伦理道德的审美观念。《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而无邪,是孔子诗学批评的重要原则。他将这一原则用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上,要求诗有雅正中和之美,如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对于其认为有失雅正中和之美倾向的“郑卫之声”提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也。”(《论语?阳货》),以“郑声淫”,故欲“放郑声”(《论语?卫灵公》)。儒家诗教崇尚雅正的传统始终被遵从和提倡。但这些文学问题的论述往往是片段的、散漫的、结论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诗、乐、舞等表现艺术相对发达的历史特征便可以在儒家以礼乐来建构文化的独特方式中找到根据。但在内容上,由于“礼”的等级观念始终规范着“乐”的自由想象,致使艺术的形式发展得不到观念更新的配合与支持,以至于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模式中转圈子,由中庸而平庸。于是,由最初富有创造性变成了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异化。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与道家的互补便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古典美学才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从而创造着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
关于文艺接受方面
孟子主张“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强调从作家作品角度去鉴赏;道家则强调发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老子提出自身要“涤除玄鉴”《老子·(十章》,)以虚静状态去感受作品之美。庄子更从虚静基础上提出“心斋”的自我提升方法。
由此可见,老、庄对艺术法则的解构,只是要摒弃人为的功利标准,并不是要践踏客观的自然规律;相反的,在处理自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上,道家的主张法则则是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意的。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它们在文艺接受的主张,无论是作品角度去鉴赏,还是发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一点你来讲,它们应该得以互补。
事实上,正是在先秦儒家与道家文艺思想在各方面上的互补所形成的必要的张力的推动下,中国美学才可能显示出多彩的风格并得到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