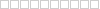近代儒学的困境
自汉代以来,儒家一直处于一种独尊的地位,虽然儒家自身的包容性和劝诱性的品性,并不导致对别的观念体系如佛教、道教的绝对排斥,但是因为儒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使得其权威性、经典性地位得到权力的保护。而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存在,使得儒家传播与权力和利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近代以来儒家面临着复杂的局面,科举制度在八股文和大量的“捐纳”(以钱买功名)冲击之下,日趋衰落,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军阀势力的崛起,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绅士阶层不断分化,儒学的传播和社会控制力,已经逐步失去了制度化的保障,进而失去独尊的地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治外法权”保护之下,基督教传教活动获得了合法性,传教士享有特权,他们采用“科学传教”的方法,即通过兴办教育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为手段来树立传教士的形象及最终达到传教目的的做法,使一向被儒生所独占的话语权力和儒生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权,均被传教士所分享。
当然,对于儒家和儒学而言,最为严重的冲击来自战争的失败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民生的艰辛和在外力面前的无力,导致人们对于作为整个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的儒学产生普遍的怀疑,儒家不再是真理的理所当然的代言者了。
与此同时,西方的知识体系,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19世纪60年代,以学习外国文字、培养对外交往人才为目标的同文馆设立后,虽然实际的运作并不顺利,如当时有人提议开设天文、算学馆,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还用“用夷变夏”这样的大帽子来打压。后来勉强可以招生了,但几乎没什么人报考,原因是这些知识当时被视为“奇技淫巧”,不像学习儒学,参加科举这样被视为“正途”。
到了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洋务学堂的开设,一些官办或官督民办企业的创立,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已经被一部分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当时争论的要点已经不在于是否要学习西方而在于到底应向西方学什么。“中体西用”是当时流行的口号,对于西方知识的称呼,也由原初的“夷学”转变为“西学”。
到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乐于用“新学”之名代替“西学”,主张“居今日欲尚西学,莫如先变其名曰新学”(范思祖《华人宜习西学仍不能废中学论》,《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二)。理由是圣人就有“其命维新”的说法。这种名称的改变其实还蕴涵着复杂的心理原因,即可以让人不致太注意中西之间的差别,避免保守势力用闭关自守的思维模式来阻止人们引进新思想。
从儒家思想本身而言,近代的思想家在保国、保教、保种的多种压力之下,对儒学本身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应对,努力对其进行新的转化,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不管这种调整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比如他们努力扩大儒学的包容性,曾国藩说儒学有“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在传统的“义理、辞章、考据”基础上,特别加上经济,凸显了经世思想在儒学中的意义,这也是整个晚清儒学的基调。
这种经世精神和西方科学精神的结合甚至带来了长期被冷落的诸子学在近代的复兴。一方面,大量被尘封已久的诸子学著作被挖掘出来,加以考订、注释;另一方面,墨家、道家、名家的思想被认为是可与儒家思想互相补充。这种观点被时人所接受和发扬,有的人开始将诸子学和西方思想结合起来,比如将墨学和逻辑学结合起来,将管子和管理学结合起来等,试图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找到更多的解决现实困境的方法。
在“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下,儒学在尽其可能地吸收西学的成分,最典型的如康有为,甚至将春秋中的“三世说”和君主立宪相结合,试图用基督教教会的方式而使儒家成为国教,如此等等。
但是,儒家的独尊地位最终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儒学内部的批评力量越来越尖锐,特别是谭嗣同的《仁学》,公开对儒家的支柱性体制“名教”和“礼教”提出激烈的批评,而康有为等人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客观上正如他的反对者所说,导致了人们对于经典的普遍的不信任。
特别是晚清以西方为榜样的社会改革,日益侵蚀着儒家思想的价值空间。以西方知识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制度的确立取代了科举制度,大众传播的出现使知识的传授和接受更加受极端性的观念所左右,特别是新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儒家的“亲亲尊尊”观念被平等和自由所取代。这种变化使儒家思想不再成为确立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同时它也失去了制度化的保障,而成为无根的“游魂”。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