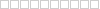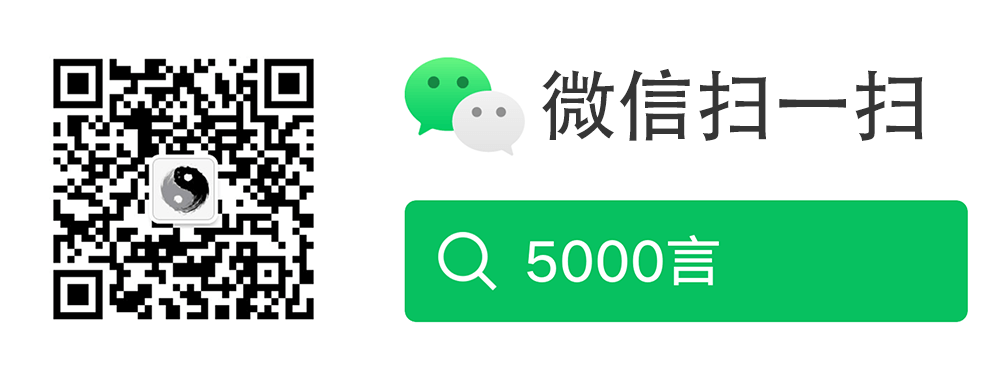中西初期的交涉
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话,在绪论中,业已说过了。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之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则是希腊文明,播布于东方的,从中国陆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后,即有输入。其后大食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其余的文明,无论其为物质的、精神的,对社会上所生的影响,更其“其细已甚”。所以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西人的东来,有海陆两路,而海路又分两路:(一)自大西洋向东行,于公元1516年绕过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国。(二)自大西洋向西行,于1492年发见美洲,1519年环绕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势力的是西、葡,后来英、荷继起,势力反驾乎其上。但其在中国,因葡萄牙人独占了澳门之故,势力仍能凌驾各国,这是明末的情形。清初,因与荷兰人有夹攻台湾郑氏之约,许其商船八年一到广东,然其势力,亦远非葡萄牙之敌。我们试将较旧的书翻阅,说及当时所谓洋务时,总是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的。的确,我们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触,不外乎这两件事。通商本两利之道,但这时候的输出入品,还带有奢侈性质,并非全国人所必需,而世世西人的东来,我们却自始对他存着畏忌的心理。这是为什么呢?其(一)中国在军事上,是畏恶海盗的。因为从前的航海之术不精,对海盗不易倾覆其根据地,甚而至于不能发现其根据地。(二)中国虽发明火药,却未能制成近世的枪炮。近世的枪炮,实在是西人制成的,而其船舶亦较我们的船舶为高大,军事上有不敌之势。(三)西人东来的,自然都是些冒险家,不免有暴横的行为。而因传教,更增加了中国畏忌的心理。近代基督教的传布于东方,是由耶稣会(Jesuit)开始的。其教徒利玛窦(Matteo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门,时为明神宗万历五年。后入北京朝献,神宗许其建立天主堂。当时基督教士的传教,是以科学为先驱;而且顺从中国的风俗,不禁华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于是在中国的反应,发生两派:其(一)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学,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正因其人学艺之精,传教的热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当时,科学的价值,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后一派的见解,自然容易得势。但是输入外国的文明,在中国亦由来已久了。在当时,即以历法疏舛,旧有的回回历法,不如西洋历法之精,已足使中国人引用教士,何况和满洲人战争甚烈,需要教士制造枪炮呢?所以1616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传播后,到1621年,即因命教士制造枪炮而复解禁。后更引用其人于历局。清初,汤若望(JoannesAdamsSchallvonBell)亦因历法而被任用。圣祖初年,为杨光先所攻击,一时失势。其后卒因旧法的疏舛,而南怀仁(FerdinandusVerbiest)复见任用。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然他对于西洋人,根本上仍存着一种畏恶的心理。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是无怪其然的。在中国一方面,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适又有别一派教士,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祟拜偶像。于是教皇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变其主张,且处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教士传教中国者,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此亦为中西隔阂之一因)。至1717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许之。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但这是从推理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15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其时可萨克族又附俄(Kazak,即哥萨克),为之东略。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骚扰且及于黑龙江。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至三藩既平,圣祖乃对外用兵。其结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条约》。订定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此约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伏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当《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中、俄的边界问题,还只限于东北方面。其后外蒙古归降中国,前此外蒙古对清,虽曾通商,实仅羁縻而已。于是俄、蒙的界务,亦成为中、俄的界务。乃有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规定额尔古讷河以西的边界,至沙宾达巴哈为止。自此以西,仍属未定之界。至1755、1759两年,中国次第平定准部回部,西北和俄国接界处尤多,其界线问题,亦延至咸丰时方才解决。
近代欧人的到广东来求通商,事在1516年,下距五口通商时,业经300余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国讫未觉得其处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还是一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清开海禁,事在1685年。于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四处。其后宁波的通商,移于定海,而贸易最盛于广东。当时在中国方面,贸易之权,操于公行之手,剥削外人颇深。外人心抱不平,乃舍粤西趋浙。1758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关封闭,驱归广东。于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国曾于1792、1810年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要求改良通商办法,均未获结果。其时中国官吏并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给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系间接。自1781年以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其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办的。1834年,公司的专利权被废止。中国说散商不便制驭,传令其再派大班。英人先后派商务监督和领事前来中国都仍认为是大班,官厅不肯和他平等交涉。适会鸦片输入太甚,因输出入不相抵,银之输出甚多。银在清朝是用为货币的,银荒既甚,财政首受其影响。遂有1839年林则徐的烧烟。中、英因此酿成战衅。其结果,于1842年在南京订立条约。中国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行商。中、英两国官员,规定了交际礼节。于是前此以天朝自居,英国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及贸易上的制限都除去了。英约定后,法、美、瑞典,遂亦相继和中国立约。惟俄人仍不许在海口通商。中西积久的隔阂,自非用兵力迫胁,可以解除于一时。于是又有1857年的冲突。广州失陷,延及京、津。清文宗为之出奔热河。其结果,乃有1858年和1860年《天津》、《北京》两条约。此即所谓咸丰戊午、庚申之役。此两次的英、法条约,系将五口通商以后外人所得的权利,作一个总结束的。领事裁判,关税协定,内地通商及游历、传教,外国派遣使臣,都在此两约中规定。美国的《天津条约》,虽在平和中交换,然因各约都有最惠国条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权利,美国亦不烦一兵而得享之。至于俄国,则自19世纪以还,渐以实力经营东方。至1850年顷,黑龙江北之地,实际殆已尽为所据。至1858年,遂迫胁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瑷珲条约》,尽割黑龙江以北,而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作为两国共管。1860年,又借口调停英、法战事,再立《北京条约》,并割乌苏里江以东。而西北边界,应当如何分划,亦在此约中规定了一个大概。先是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方面,已许俄国通商,至是再开喀什噶尔,而海口通商及传教之权,亦与各国一律。而且规定俄人得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进京。京城和恰克图间的公文,得由台站行走。于是蒙古、新疆的门户,亦洞开了。总而言之:自1838年林则徐被派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起,至1860年各国订立《北京条约》为止,中国初期与外国交涉的问题,告一结束。其所涉及的,为:(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内地通商、游历、传教,(三)税则,(四)审判,(五)沿海航行,(六)中、俄陆路通商,及(七)边界等问题。汉族的光复运动
一个民族,进步到达于某一程度之后,就决不会自忘其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了。虽然进化的路径,是曲线的,有时不免暂为他族所压服。公元1729,即清世宗的雍正七年,曾有过这样一道上谕。他说:“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蛊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这一道上谕,是因曾静之事而发的。曾静是湖南人,读浙江吕留良之书,受着感动,使其徒张熙往说岳钟琪叛清,钟琪将其事举发。吕留良其时已死,因此遭到了剖棺戮尸之祸。曾静、张熙暂时免死拘禁,后亦被杀。这件事,向来被列为清朝的文字狱之一,其实乃是汉族图谋光复的实际行动,非徒文字狱而已。1729年,为亡清入关后之八十六年,表面上业已太平,而据清世宗上谕所说,则革命行动的连续不绝如此,可见一部分怀抱民族主义的人,始终未曾屈服了。怀抱民族主义的人,是中下流社会中都有的。中流社会中人的长处,在其知识较高,行动较有方策,且能把正确的历史知识,留传到后代,但直接行动的力量较弱。下流社会中人,直接行动的力量较强,但其人智识缺乏,行动起来,往往没有适当的方策,所以有时易陷于失败,甚至连正确的历史,都弄得缪悠了。清朝最大的会党,在北为哥老会,在南为天地会,其传说大致相同。天地会亦称三合会,有人说就是三点会,南方的清水、匕首、双刀等会,皆其支派。据他们的传说:福建莆田县九连山中,有一个少林寺。僧徒都有武艺。曾为清征服西鲁国。后为奸臣所谗,清主派兵去把他们剿灭。四面密布火种,缘夜举火,想把他们尽行烧死。有一位神道,唤做达尊,使其使者朱开、朱光,把十八个和尚引导出来。这十八个和尚,且战且走,十三个战死了。剩下来的五个,就是所谓前五祖。又得五勇士和后五祖为辅,矢志反复汨。就是清字,汨就是明字,乃会中所用的秘密符号。他们自称为洪家。把洪字拆开来则是三八二十一,他们亦即用为符号。洪字大约是用的明太祖开国的年号洪武;或者洪与红同音,红与朱同色,寓的明朝国姓的意思,亦未可知。据他们的传说:他们会的成立,在1674年。曾奉明思宗之裔举兵而无成,乃散而广结徒党,以图后举。此事见于日本平山周所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平山周为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曾身入秘密社会,加以调查)。据他说:“后来三合会党的举事,连续不绝。其最著者,如1787,即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之变便是。1832,即宣宗道光十二年,两广、湖南的瑶乱,亦有三合会党在内。鸦片战争既起,三合会党尚有和海峡殖民地的政府接洽,图谋颠覆清朝的。”其反清复明之志,可谓终始不渝了。而北方的白莲教徒的反清,起于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四省,至1804年,即仁宗嘉庆九年而后平定,此即向来的史家称为川、楚教匪,为清朝最大的内乱之始的,其所奉的王发生,亦诈称明朝后裔,可见北方的会党,反清复明之志,亦未尝变。后来到1813年,即嘉庆十八年,又有天理教首林清,图谋在京城中举事,至于内监亦为其内应,可见其势力之大。天理教亦白莲教的支派余裔,又可见反清复明之志,各党各派,殊途同归了。而其明目张胆,首传讨胡之檄的则为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系广东花县人。生于1812年,恰在民国纪元之前百年。结合下流社会,有时是不能不利用宗教做工具的。广东和外人交通早,所以天王所创的宗教,亦含有西教的意味。他称耶和华为天父,基督为天兄,而己为其弟。乘广西年饥盗起,地方上有身家的人所办的团练和贫苦的客民冲突,以1850年,起事于桂平的金田村。明年,下永安,始建国号。又明年,自湖南出湖北,沿江东下。1853年,遂破江宁,建都其地,称为天京。当天国在永安时,有人劝其北出汉中,以图关中;及抵武、汉时,又有人劝其全军北上;天王都未能用。既据江宁,耽于声色货利,不免渐流于腐败。天王之为人,似只长于布教,而短于政治和军事。委政于东王杨秀清,尤骄恣非大器。始起诸王,遂至互相残杀。其北上之军,既因孤行无援,而为清人所消灭。溯江西上之兵,虽再据武、汉,然较有才能的石达开,亦因天京的政治混乱,而和中央脱离了关系。清朝却得曾国藩,训练湘军,以为新兴武力的中坚。后又得李鸿章,招募淮军,以为之辅。天国徒恃一后起之秀的李秀成,只身支柱其间,而其余的政治军事,一切都不能和他配合。虽然兵锋所至达十七省(内地十八省中,惟甘肃未到),前后共历十五年,也不得不陷于灭亡的悲运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其责实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他的兵力,是够剽悍的。其扎实垒、打死仗的精神,似较之湘、淮军少逊,此乃政治不能与之配合之故,而不能悉归咎于军事。若再推究得深些,则其失败,亦可以说是在文化上。(一)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中国的下流社会中人,是向来有均贫富的思想的,其宗旨虽然不错,其方策则决不能行。今观太平天国所定的把天下田亩,按口均分;二十五家立一国库,婚丧等费用,都取给国库,私用有余,亦须缴入国库等;全是极简单的思想,极灭裂的手段。知识浅陋如此,安能应付一切复杂的问题?其政治的不免于紊乱,自是势所必然了。(二)满洲人入据中原,固然是中国人所反对,而是时西人对中国,开始用兵力压迫,亦为中国人所深恶的,尤其是传教一端,太平天国初起时,即发布讨胡之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读之亦使人气足神王。倘使他们有知识,知道外力的压迫,由于满清的失政,郑重提出这一点,固能得大多数人的赞成;即使专提讨胡,亦必能得一部分人的拥护。而他们后来对此也模糊了,反而到处传播其不中不西的上帝教,使反对西教的士大夫,认他为文化上的大敌,反而走集于清朝的旗帜之下。这是太平天国替清朝做了掩蔽,而反以革命的对象自居,其不能成事,实无怪其然了。湘、淮军诸将,亦是一时人杰。并无一定要效忠于满清的理由,他们的甘为异族作伥,实在是太平天国的举动,不能招致豪杰,而反为渊驱鱼。所以我说他政治上的失败,还是文化上的落后。
和太平天国同时的,北方又有捻党,本蔓延于苏、皖、鲁、豫四省之间。1864年,天国亡,余众多合于捻,而其声势乃大盛。分为东西两股。清朝任左宗棠、李鸿章以攻之。至1867、1868两年,然后先后平定。天国兵锋,侧重南方,到捻党起,则黄河流域各省,亦无不大被兵灾了,而回乱又起于西南,而延及西北。云南的回乱,起于1855年,至1872年而始平,前后共历十八年。西北回乱,则起于1862年,自陕西延及甘肃,并延及新疆。浩罕人借兵给和卓木的后裔,入据喀什喀尔。后浩罕之将阿古柏帕夏杀和卓木后裔而自立,意图在英、俄之间,建立一个独立国。英、俄都和他订结通商条约,且曾通使土耳其。英使且力为之请,欲清人以天山南北路之地封之。清人亦有以用兵劳费,持是议者。幸左宗棠力持不可。西捻既平之后,即出兵以攻叛回。自1875至1878,前后共历四年,而南北两路都平定。阿古柏帕夏自杀。当回乱时,俄人虽乘机占据伊犁,然事定之后,亦获返还。虽然画界时受损不少,西北疆域,大体总算得以保全。
清朝的衰机,是潜伏于高宗,暴露于仁宗,而大溃于宣宗、文宗之世的。当是时,外有五口通商和咸丰戊午、庚申之役,内则有太平天国和捻、回的反抗,几于不可收拾了。其所以能奠定海宇,号称中兴,全是一班汉人,即所谓中兴诸将,替他效力的。清朝从道光以前,总督用汉人的很少,兵权全在满族手里。至太平天国兵起,则当重任的全是汉人。文宗避英、法联军,逃奔热河,1861年,遂死于其地。其时清宗室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握权。载垣、端华亦是妄庸之徒,肃顺则颇有才具,力赞文宗任用汉人,当时内乱的得以削平,其根基实定于此。文宗死,子穆宗立。载垣、端华、肃顺等均受遗诏,为赞襄政务大臣。文宗之弟恭亲王奕诉,时留守京师,至热河,肃顺等隔绝之,不许其和文宗的皇后钮钴禄氏和穆宗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相见。后来不知如何,奕诉终得和他们相见了,密定回銮之计。到京,就把载垣、端华、肃顺都杀掉。于是钮钴禄氏和叶赫那拉氏同时垂帘听政(钮钴禄氏称母后皇太后,谥孝贞。叶赫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死谥孝钦。世称孝贞为东宫太后,孝钦为西宫太后),钮钴禄氏是不懂得什么的,大权都在叶赫那拉氏手里。叶赫那拉氏和肃顺虽系政敌,对于任用汉人一点,却亦守其政策不变,所以终能削平大难。然自此以后,清朝的中央政府即无能为,一切内政、外交的大任,多是湘、淮军中人物,以疆臣的资格决策或身当其冲。军机及内阁中,汉人的势力亦渐扩张。所以在这个时候,满洲的政权,在实际上已经覆亡了,只因汉人一方面,一时未有便利把他推倒,所以名义又维持了好几十年。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