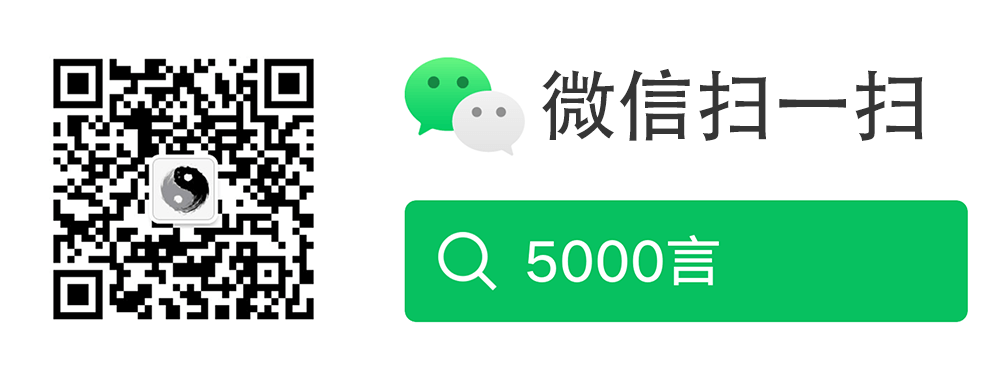非命(中)
从“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墨子认为国家的兴亡、个人的富贵贫贱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而主要是主观的努力。在这里他提出了统治者的主观努力对天下的治乱起着决定的作用,给以儒家为代表的命定论者以沉重的打击,但因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所以他把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从不可知的“命运”搬到少数圣王的手中,他认为夏桀、商纣王等人之所以会乱天下,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自己不努力的结果。他的这种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同时他认为“天下之治”是“商汤、周武王”等人的力量,这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处在那种情况下,不是商汤、周武王等人推翻他们,肯定也还会有别人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