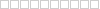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话说贾臬台的大少爷,自从造了一封周中堂的假信,吹了个风声到河台耳朵里,竟把河台瞒过,信以为真,立刻委他当了河工下游的总办。他心十分欢喜,立刻上辕禀见谢委禀辞。河台见面之后,不免又着实灌些米汤。他到工之后,自己一个人盘算:“将来大工合龙,随折保个送部引见,已在掌握之中。虽然免了指省、保举一切费用,然而必得放个实缺出来,方满我的心愿。”又想:“要放实缺,非走门路不可;要走门路,又非花钱不可。”因此他一到工上,先把前头委的几个办料委员抓个错,一齐撤差,统通换了自己的私人,以便上下其手。下游原有一个总办,见他如此作威作福,心上老大不高兴,屡次到河台面前说姓贾的坏话。河台碍于情面不好将他如何。后来又被贾总办晓得了,反说他有意霸持,遇事掣肘,递了个禀帖给河台,请河台撤他的差使,以便事权归一:“大人若不将他撤去,职道情愿辞差。”河台无法,只得又把前头的一个总办调往别处,这里归了他一人独办,更可以肆无忌惮,任所欲为。
诸公要晓得:凡是黄河开口子,总在三汛。到了这时候,水势一定加涨,一个防堵不及,把堤岸冲开,就出了岔子。等到过了这个汛,水势一退,这开口子的地方竟可以一点水没有。所以无论开了多大的口门,到后来没有不合龙的。故而河工报效人员,只要上头肯收留,虽然辛苦一两个月,将来保举是断乎不会漂的。此番贾大少爷既然委了这个差使,任凭他如何赚钱,只要他肯拿土拿木头把他该管的一段填满,挨过来年三汛不出乱子,他便可告无罪。就是出了乱子,上头也不肯为人受过,但把地名换上一个,譬如张家庄改作李家庄,将朝廷蒙过去,也就没有处分了。自来办大工的人都守着这一个诀窍,所以这回贾大少爷的保举竟其十拿九稳。
有话便长,无话便短。过了几日,决口地方虽不能如上文所说的点水俱无,然而水势渐平,防堵易于为力,又加以河帅恐遭严谴,昼夜督催。贾大少爷本是个娇生惯养的人,到了此时,也只好跟在工上吃辛吃苦,亦总算难为他了。等到工程十成八九,大众方才把心放下。下游工程统归总办作主,当由他选择吉日吉时合龙。到了那天四更头里,贾大少爷换了一身簇新的行装,摆齐亲兵小队,跨了一匹高头大马,亲到工上督率。等着吉时报到,大工告成,总办又统率在工大小文武员弁上香行礼,叩谢河神。文武员弁又一齐向总办贺喜,总办又赴河帅行辕禀知合龙。当蒙河帅传见,允为从优保奖。照例文章,不用细述。贾大少爷事完之后,当即回省,仍在父亲衙内居住。过了些时,电报局得了阁抄上谕,晓得贾大少爷蒙河督于奏报合龙折内,另片奏保,奉旨送部引见,先赏加布政使衔。得信之下,自然欢喜。河督因他是贾臬台的少爷,乃是同寅之子,虽未接到部文,业奉圣旨允准,特地先写信来关照。贾臬台便叫儿子先赴河督、巡抚两院叩谢。此时督、抚两宪俱已开复处分,而且一齐又交部从优议叙,自然也是高兴的。等到大案出奏的时候,贾大少爷除将在工员弁分别异常、寻常请奖外,又趁势把自己的兄弟侄儿、亲戚故旧,蒙保了十几个在里头。河督一时不及细察,统通保了进去。这是河工上的积弊如此,也无从整顿的。
闲话休提。单说贾大少爷这一趟差使,钱也赚饱了,红顶子也戴上了,送部引见也保到手了,正是志满心高,十分得意。在家里将息了两个月,他便想进京引见,谋干他的前程。禀告父亲,贾臬台自然无甚说得,随向原保大臣那里请了咨文,择日登程北发。预先把赚来的银子托票号里替他汇十万进京。又托京里朋友预为代赁高大公馆一所,以便到京居住。诸事办妥,然后自己带了一个姨太太,一个代笔师爷,又一个管帐的,并男女大小仆人、厨子、车夫人等,数了数足足有三十来个。贾大少爷同姨太太坐的都是自己的车,其余全是祥符县办的官车。在路晓行夜宿,非止一日。一日到得北京城,在顺治门外南横街,朋友替他预先找好的一座公馆暂时住下。贾大少爷此番进京原是为广通声气起见,所以打定主意,极力拉拢。到京之后,凡是寅、年、世、戚、乡谊,无不亲自登门奉拜,足足拜了七八天的客方才拜完。他每日出门,坐的是自己的坐车。骡子是在河南五百两银子买的,赶车的一齐头戴羽缨凉帽,身穿葛布袍子,腰挂荷包,足登抓地虎,跨在车沿上,脊梁笔直,连帽缨子都不作兴动一动,这个名堂叫做“朝天一炷香”。京城里顶讲究这个,所以贾大少爷竭力摹仿。坐车之外,前顶马,后跟骡,每到一处,管家赶忙下马,跑在前头投帖。所拜的客,也有见得着的,也有见不着的,也有发帖子请吃饭的,也有过天来回拜的。贾大少爷都不在意,顶要紧的是太老师周中堂同着寄顿银子一个钱店掌柜,外号叫做黄胖姑的,到京的第二天就去奉拜。
齐巧这天周中堂请假在家,一见大片子名字上头写着“小门生”三个字,另外粘着一张签条,写明“河南按察使贾某之子”,周中堂便晓得是他了。这位老中堂一直做京官,没有放过外任,一年四季,什么炭敬、冰敬、贽见、别仪,全靠这班门生故吏接济他些,以资浇裹。如今听说是他,心上早打了底子,立刻请见。贾大少爷进去了好一回,只觉得冷冷清清,不见动静。约摸坐了半个钟头中堂方才出来。贾大少爷朝他拜了几拜,中堂只还了半个揖,让他坐。他晓得中堂的炕不是寻常人可以坐得的,就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中堂见了他,气吁吁的,只问得他父亲一声“好”,跟手自己就发了一顿牢骚,随后方问:“你来京干吗?”贾大少爷一一回答。中堂见话说完,就此送客。
贾大少爷出来,忙赶到前门外大栅栏去找黄胖姑。黄胖姑是绍兴人,因为在京年久,说的一口好京话,京城上下三等人都认得,外省官场也很同他拉拢。大家为他养的肥胖,做起事来又有些婆婆妈妈的腔调,所以大家就送他一个表号,叫他做黄胖姑。他这表号是没有一个人不晓得的。贾大少爷到他店门口下了车,不等通报,闯进了门就嚷着问道:“胖姑在家没有?”惹得一班伙计们都抿着嘴笑。一个伙计把他领到客座里。只听得嘻嘻哈哈一阵笑声,从里头笑到外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黄胖姑。黄胖姑一见贾大少爷,嘴里嚷道:“我的大爷,你是几时来的?可把我想坏了!”贾大少爷要同他行礼,他双手拉住贾大少爷的手,不准他下礼,那股要好的劲,画亦画不出。两人分宾叙坐。才坐下,黄胖姑又站起来问:“老大人好?”贾大少爷亦站起来回答说:“好。”然后仍旧坐下对谈。黄胖姑要留贾大少爷吃便饭,贾大少爷道:“今天要拜客,过天再扰罢。”黄胖姑便问:“今天拜了些什么客?”贾大少爷回称:“刚从周中堂那里来。”黄胖姑道:“这位老中堂现在背时的了,你去找他做啥?”贾大少爷一听大惊,急于要问。黄胖姑道:“新近他老人家因为误保了一个人,上头很不喜欢,着实拿他申饬,几乎把官送掉,亏了一位王爷替他求情,官虽没有坏,恐怕要去军机,所以他这两天请假躲在家里。你想,出了军机,还有什么捞呢?”贾大少爷听说,心上沉思道:“怪不得走上大门冷清清,见了他老人家面色很不对,又发了半天牢骚,原来就是这个讲究。”想罢问道:“保着一个什么人保举错了?”黄胖姑道:“本来老中堂也太糊涂了!什么人保不得,偏偏保举个维新党,怎么不要坏官呢!赶出军机还是便宜他的。”贾大少爷顿脚说道:“糟了,糟了!里头顶恨这个,他老人家怎么糊涂到这步地位!他保举维新党,人家就要疑心他,连他亦是个维新党。”黄胖姑道:“对啊!正是为此。”贾大少爷道:“既然如此,以后他那里我亦不便常去走动,省得叫人家疑心,说我也是他们同党。”黄胖姑把大拇指头一伸道:“我的大爷,你真是个明白人,有见识!我佩服你!况且这种背时的人,你巴结他也没用。”
贾大少爷听了,半天不语。黄胖姑何等刁钻,早已瞧出他是因为断了一条门路,心上可惜的意思。便说道:“他的事是自己找的,我们也不必顾恋他。大爷,咱是自己人,你的事情我总可以效力。我有几个朋友在里头,大家都还说得来,你委了我,我去托他们,包你成功就是了。”贾大少爷一听这话,句句打入他的心坎,霎时转忧为喜,连说:“本来有许多事要拜托费心。……过天细细的再谈。”说完起身,要往别处拜客。黄胖姑又恐怕买卖被人家分做了去,不肯放松一步,先约他明天到便宜坊吃中饭,又道:“大爷早晨出门拜客,可以到馆子里去换便衣,咱们尽兴乐一乐。”贾大少爷立时应允。临时出来上车,忽然又笑着问黄胖姑道:“近来有什么好‘条子’没有?”黄胖姑道:“有有有,明天我荐给你。”说完各自分手。
黄胖姑回转店内,立刻写帖子请客。所请的客,一位是新科翰林钱运通钱太史;一位是甲班主事王占科王老爷;一位是个宗室老爷,名字叫做溥化,排行第四,人家都尊他为溥四爷;一位是银炉老板,姓白号韬光;一位是琉璃厂书铺掌柜的,姓黑,名字叫做黑伯果,天生一张嘴,能言惯道,一到席面上,咭咭呱呱,只有他一个人说的话,大家叫顺了嘴,把黑伯果三个字竟变为“黑八哥”了;还有一位,是在前门外开古董铺的,姓刘名厚守,新近捐了一个光禄寺署正,常常带着白顶子同大人先生们来往。这些人除去钱、王二位是带还东的,其余全是黄胖姑的好友,而且广通内线,专拉皮条。黄胖姑看准了,想做贾大少爷一注生意,所以把这些人一齐邀来。当下数了数,连贾大少爷一共是七个客人。帖子写好,派人一面到便宜坊定座,一面分头请客。不在话下。
到了次日,看看自鸣钟上刚正打过十一点,黄胖姑吩咐套车,自己先到便宜坊等候。约摸有三刻工夫,黑八哥头一个先来。第二个便是宗室溥四爷,一进门就同黄胖姑请安拉手,说不出那副亲热样子。贾大少爷虽然沿途拜客,倒也未曾耽搁,接着也就来了。一个个问“贵姓、台浦”,黄胖姑替他们三个彼此通姓报名,大家无非说了些“久仰”的客气话。后来说到溥四爷,黄胖姑说:“贾大哥!我们这位溥老弟乃是宗室当中第一位博学。”说罢,又哈哈一笑道:“谁不晓得北京城里有名的才子溥四爷呢!我从前考过他的学问:我拿笔在纸上写一竖两点,他认得是个小的‘小’字;后来我又在小字上头加了两横,难为他亦认得,说是出告示的‘示’字;跟手我又在示字上加了一个宝盖头,他说这是我们宗室的‘宗’字。这些都不稀奇,末后来又在宗字头上加一个山字,这却难为他了,你说他念个什么字?”贾大少爷尚未接言,黄胖姑道:“他说是哈哒门的‘哈’字。大爷,你瞧,亏他好记性,记得这字是哈哒门的‘哈’字。”贾大少爷也明白,北京城的崇文门俗名叫做哈哒门,想是溥四爷念惯了“哈”字,看惯了“崇”字,所以拿“崇”字当作“哈”字读了。晓得这话是黄胖姑奚落溥四爷的,但系初次相会,不便说什么,只好笑而不答。及至回头再看,溥四爷却是眉头一掀,脖子一挺,欲笑不笑的满面孔得意之色。
大家言来语去,正谈论间,白韬光、刘厚守、钱太史三个人亦都来到。其时已有四点多钟,只差王主事一个人。黄胖姑道:“时候不早了,我们先坐罢,空了首席等他。”刚才入座停当,人报王老爷来,大家一齐站起,主人出位相迎。只见王主事穿着衣帽进来,先朝主人作了一个揖,又朝台面上作了一个总揖。黄胖姑让他换了便衣入座。在席的人,王主事只认得钱太史及古董铺老板刘厚守两个人。钱太史发达比他迟两科,乃是后辈,并不在意。倒是这刘厚守,乃是一直充当现任满大学士、又兼军机大臣华中堂的门上,跟了中堂几年,着实发了几十万银子的家私,因此就在前门外开了一爿古董铺,如今虽然捐了官,却还常到中堂宅内当差。王主事还是那年朝考,中堂派了阅卷大臣,照例拜门去过几趟,没有得见,只好在刘厚守门房里坐坐。刘厚守虽不认得他,他却记得刘厚守的面孔。自古道:“宰相家奴七品官。”况且他现在又捐了署正,同是六品,一样分印结,而且又是中堂老师的门口,寻常人那里巴结得上。如今反见他坐在下首,自己坐了首坐,心上着实不安,一定要同刘厚守换坐。刘厚守不肯道:“你别光让我,还有别人呢。”王主事只得又让别人,别人都不肯,只得自己扭扭捏捏的坐了。然后同不认得的人,一一问“贵姓、台甫”,“贵科、贵班、贵衙门”。一问问到贾大少爷,贾大少爷回称:“姓贾,号润孙。”黄胖姑插口说道:“这位便是河南臬台贾筱芝贾大人的少爷,我们至好。”王主事道:“原来是孝子顺孙,聚在一门,难得难得!”跟手又问:“贵科?”贾大少爷涨红了脸,回答不出。黄胖姑只得又替他说道:“这位贾观察乃是去年赈捐案内保过道班,今年河工合龙,又蒙河台保了送部引见。他老大人官声甚好,早已简在帝心,将来润翁引见之后,指日就要放缺的。”王主事一听他不是科甲出身,立刻回转了脸不同他说话。在座的人只有同钱太史还说得来。王占科乃是“庶常散”的主事,钱运能乃是新庶常,所以钱运通见了王占科竟其口口声声“老前辈”,自称“晚生”。王主事却是直受不辞,非凡得意。
不料谈了半天,刘厚守忽然问王主事道:“王老爷你好面善,我们好像在那里会过?”一句话问住了。王主事羞得满脸通红,歇了半天才答道:“厚翁,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兄弟那年朝考下来,三次到中堂老师那里去叩见,回回都坐在厚翁的屋子里,怎么就忘记了?”刘厚守道:“莫怪,莫怪!我们中堂,每日找他的人可不少,咱那里记得许多。不要说别的,外省实缺藩、臬来过几次,我还记不清他的名字,何况……”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黄胖姑赶忙打岔道:“这位王大哥乃是刑部主事,贵州司行走,当差很勤。将来老中堂跟前,还得你老哥保举保举他,常常提提他名字,拜托拜托!”刘厚守听了一笑。王主事更觉难以为情,坐立不定。
这个档口里,贾大少爷坐着无味,便做眉眼与黄胖姑。黄胖姑会意,晓得他要叫“条子”,本来也觉着大家闷吃不高兴,遂把这话问众人,众人都愿意。黄胖姑便吩咐堂倌拿纸片。当下纸笔拿齐,溥四爷头一个抢着要写,先问:“王老爷叫那一个?”王老爷说:“二丽。”无奈溥四爷提笔在手,欲写而力不从心,半天画了两画,一个“丽”字写死写不对,后来还是王老爷提过笔来自己写好。当下检熟人先写,于是刘厚守叫了一个景芬堂的小芬。黑伯果叫了一个老相公,名字叫绮云。白韬光说:“我没有熟人,我免了罢。”主人黄胖姑倒也随随便便。不料溥四爷反不答应,拉着他一定要叫。白韬光道:“如要我破例叫条子,对不住,我只好失陪了。”大家见他要走,只得随他。钱运通说:“老前辈在这里,不敢放肆。”王老爷不去理他,早已替他写好了。溥四爷最高兴,叫了两个:一个叫顺泉,一个叫顺利。末后轮到贾大少爷。王老爷因为他是捐班,瞧他不起,不同他说话,只问得黄胖姑一声说:“你这位朋友叫谁?”贾大少爷叫黄胖姑荐个条子。黄胖姑想了一回,忽然想到韩家潭喜春堂有个相公名叫奎官。他虽不叫这相公的条子,然而见面总请安,说:“老爷有什么朋友,求你老赏荐赏荐!”因此常常记在心上。当时就把这人荐与贾大少爷。主人见在台的人都已写好,然后自己叫了一个小相公红喜作陪。霎时条子发齐,主人让菜敬酒。
不多一会,跑堂的把门帘一掀,走了进来,低着头回了一声道:“老爷们条子到了。”众人留心观看,倒是钱太史的相好头一个来。这小子长的雪白粉嫩,见了人叫爷请安,在席的人倒有一大半不认得他。问起名字,王老爷代说:“他是庄儿的徒弟,今年六月才来的。头一个条子就是我们这位钱运翁破的例。你们没瞧见,运翁新近送他八张泥金炕屏,都是楷书,足足写了两天工夫。另外还有一副对子,都是他一手报效的。送去之后,齐巧第二天徐尚书在他家请客。他写的八张屏挂在屋里,不晓得被那位王爷瞧见了,很赏识。”说至此,钱太史连连自谦道:“晚生写的字,何足以污大人先生之目!……不过积习未除,玩玩罢了。”王占科道:“这是他师傅庄儿亲口对我讲的,并不假。照庄儿说起来,运翁明年放差大有可望。”大众又一齐向钱太史说“恭喜”。
正闹着,在席的条子都络续来到,只差得贾大少爷的奎官没来。这时候贾大少爷见人家的条子都已到齐,瞧着眼热,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甚觉没精打采。黄胖姑看出苗头,便说:“奎官的条子并不忙,怎么还不来?”正待叫人去催,奎官已进来了,黄胖姑便把贾大少爷指给他。奎官过来请安坐下,说:“今日是我妈过生日,在家里陪客,所以来的迟了些,求老爷不要动气!”溥四爷说道:“你再不来,可把他急死了。”一头说话,一头喝酒。叫来的相公搳拳打通关,五魁、八马,早已闹的烟雾尘天。贾大少爷便趁空同奎官咬耳朵,问他:“现在多大年纪?唱的什么角色?出师没有?住在那一条胡同里?家里有什么人?”奎官一一的告诉他:“今年二十岁了。一直是唱大花脸的。十八岁上出的师,现在自己住家,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去年腊月娶的媳妇,今年上春三死了。住在韩家潭,同小叫天谭老板斜对过。老爷吃完饭,就请过去坐坐。”贾大少爷满口答应。奎官从腰里摸出鼻烟壶来请老爷闻,又在怀里掏出一杆“京八寸”,装上兰花烟,自己抽着了,从嘴里掏出来,递给贾大少爷抽。贾大少爷又要闻鼻烟,又要抽旱烟,一张嘴来不及,把他忙的了不得。一头吃烟,举目四下一看,只见合席叫来的条子都没有像奎官如此亲热巴结的,自己便觉着得意,更把他兴头的了不得。
黄胖姑都看在眼中,朝着贾大少爷点点头,又朝着奎官挤挤眼。奎官会意,等到大家散的时候,他偏落后迟走一步。黄胖姑连忙帮腔道:“大爷,怎么样?可对劲?”贾大少爷笑而不答。溥四爷嚷着,一定要贾大少爷请他吃酒:“齐巧今儿是奎官妈的生日,你俩如此要好,你不看朋友情分,你看他面上,今儿这一局还好意思不去应酬他吗?”白韬光道:“润翁赏酒吃,兄弟一定奉陪。”黑伯果拍他一下道:“不害臊的,条子不叫,酒倒会要着吃。”说的大家都笑了。贾大少爷却不过情,只得答应同到奎官家去。又托黄胖姑代邀在席诸公。王老爷头一个回头说:“明天有公事,要起早上衙门,谢谢罢!”刘厚守说:“我不能磨夜,有时候的,九点钟总得回家。”黄胖姑道:“不错,厚翁嫂夫人阃令极严,我不敢勉强。回来叫他顶灯吃苦头,是对他不住的。”又朝着钱太史说道:“运翁明天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同去走走。”贾大少爷因为他是翰林,要借他撑场面,便道:“运翁是最好没有,我们一见如故,今天一定赏光的。”钱太史无奈,只得应允。王老爷起先还想拉住钱太史,做眼色给他,叫他不要去,后来见他答应,便也无法,他自己只得跟了刘厚守,先辞别众人,上车而去。
这里大家席散,约摸已有八点多钟。等到主人看过帐,大众作过揖,然后一齐坐了车同往韩家潭而来。便宜坊到韩家潭有限的路,不多一会就到了。下车之后,贾大少爷留心观看:门口钉着一块黑漆底子金字的小牌子,上写着“喜春堂”三个字;大门底下悬了一盏门灯。有几个“跟兔”,一个个垂手侍立,口称:“大爷来啦!”走进门来,虽是夜里,还看得清爽,仿佛是座四合厅的房子,沿大门一并排三间,便是客座书房,院子里隔着一道竹篱,地下摆着大大小小的花盆,种了若干的花。
这一天是奎官妈的生日,隔着篱笆,瞧见里面设了寿堂,点了一对蜡烛,却不甚亮。有几个穿红着绿的女人,想是奎官的亲戚,此外并无别的客人,甚是冷冷清清。当下奎官出来,把众人让进客堂。贾大少爷举目四看:字画虽然挂了几条,但是破旧不堪;烟榻床铺一切陈设,有虽有,然亦不甚漂亮。一面看,一面坐下。溥四爷、白韬光两个先吵着:“快摆,让我们吃了好走。”主人无奈,只得吩咐预备酒。一声令下,把几个跟兔乐不可支,连爬带滚的嚷到后面厨房里去了。霎时台面摆齐,主人让坐,拿纸片叫条子。以及条子到,搳拳敬酒,照例文章,不用细述。
这时候贾大少爷酒入欢肠,渐渐的兴致发作,先同朋友搳通关,又自己摆了十大碗的庄。不知不觉有了酒意,浑身燥热起来,头上的汗珠子有绿豆大小。奎官让他脱去上身衣服,打赤了膊,又把辫子盘了两盘。谁知这位大爷有个毛病,是有狐骚气的,而且很利害,人家闻了都要呕的。当下在席的人都渐渐觉得,于是闻鼻烟的闻鼻烟,吃旱烟的吃旱烟。奎官更点了一把安息香,想要解解臭气。不料贾大少爷汗出多了,那股臭味格外难闻。在席的人被熏不过,不等席散,相率告辞,转眼间只剩得黄胖姑一个。奎官怕近贾大少爷的身旁,贾大少爷一定要奎官靠着他坐,奎官不肯。贾大少爷伸出手去拖他,奎官无法,只得一只手拿袖子掩着鼻子。贾大少爷是懂得相公堂子规矩的,此时倚酒三分醉,竟握住了奎官的手,拿自己的手指头在奎官手心里一连掏了两下。奎官为他骚味难闻,心上不高兴,然而又要顾黄胖姑的面子,不好直绝回复他不留他,只好装作不知,同他说别的闲话。贾大少爷一时心上抓拿不定。黄胖姑都已明白,只得起身告别,贾大少爷并不挽留。奎官一见黄老爷要走,怕他走掉,贾大少爷更要缠绕不清,便说:“求黄老爷等一等,我们大爷吃醉了,还是把车套好,一块儿把他送回家去的好。”
贾大少爷听说套车,这一气非同小可!他手里正拿着一把酒壶,还在那里让黄胖姑吃酒,忽听这话,但听得“拍秃”一声,一个酒壶已朝奎官打来。虽然没有打着,已经洒了浑身的酒。又听得“拍”的一声,桌子上的菜碗,乒乒乓乓,把吃剩的残羹冷炙翻的各处都是,幸亏台面没有翻转。奎官一看情形不对,便说道:“大爷,你可醉啦!”贾大少爷气的脸红筋涨,指着奎官大骂道:“我毁你这小王八羔子!我大爷那一样不如人!你叫套车,你要赶着我走!还亏是黄老爷的面子,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如果不是黄老爷荐的,你们这起王八羔子,没良心的东西,还要吃掉我呢!”一头骂,一头在屋里踱来踱去。黄胖姑竭力的相劝,他也不听。奎官只得坐在底下不做声。歇了半天,熬不住,只得说道:“黄老爷,你想这是那里来的话!我怕的大爷吃醉,所以才叫人套车,想送大爷回去,睡得安稳些,为的是好意。”贾大少爷道:“你这个好意我不领情!”奎官又道:“不是我说句不害臊的话,就是有什么意思,也得两相情愿才好。”贾大少爷听到这里,越发生气道:“放***的狗臭大驴屁!你拿镜子照照你的脑袋,一个冬瓜脸,一片大麻子,这副模样还要拿腔做势,我不稀罕!”奎官道:“老爷叫条子,原是老爷自己情愿,我总不能捱上门来。”贾大少爷气的要动手打他。
黄胖姑因怕闹的不得下台,只得奔过来,双手把贾大少爷捺住,说道:“我的老弟!你凡事总看老哥哥脸上。他算得什么!你自己气着了倒不值得!你我一块儿走。”贾大少爷道:“时候还早得很,我回去了没有事情做。”黄胖姑道:“我们去打个茶围好不好?”贾大少爷无奈,只得把小褂、大褂一齐穿好。奎官拗不过黄胖姑的面子,也只得亲自过来帮着张罗,又让大爷同黄老爷吃了稀饭再去。贾大少爷不理,黄胖姑说:“吃不下。”因为路近,黄胖姑说:“不用坐车,我们走了去。”于是奎官又叫跟兔点了一盏灯笼,亲自送出大门,照例敷衍了两句,方才回去。
当下二人走出门来,向南转弯,走了一截路,出得外南营,一直向东,又朝北方进陕西巷,一走走到赛金花家。黄胖姑一进门便问:“赛二爷在家没有?”人回:“赛二爷今儿早上肚子疼,请大夫吃了药,刚刚睡着了。”黄胖姑道:“既然他睡了,我们不必惊动他,到别的屋子里坐坐,就要走的。”当下就有人把他俩一领,领到一个房间里坐了。黄胖姑问:“姑娘呢?”人回:“花宝宝家应条子去了。”黄胖姑无甚说得。于是二人相对,躺在烟铺上谈心。贾大少爷一直把个奎官恨的了不得。黄胖姑因为是自己所荐,也不好同他争论什么,只说道:“论理呢,这事情奎官太固执些。你大爷也太情急了些,才摆一台酒就同他如此要好,莫怪他要生疑心。过天你再摆台饭试试如何?”贾大少爷道:“算了罢,那副嘴脸我不稀罕。我有钱那里不好使,一定要送给他!”黄胖姑道:“你的话原不错。这种事情,丢开就完了,有什么一直放在心上的。好便好,不好就再换一个,十个八个,听凭你大爷挑选,谁能够管住你呢!”贾大少爷道:“你这话很明白。我今天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早把那小鳖蛋的窠毁掉了。”
黄胖姑道:“这些话不用说了,我们谈正经要紧。你这趟到京城,到底打个什么主意?”贾大少爷便凑近一步,附耳低声,把要走门子的话说了一遍。又说:“在河南的时候,常常听见老人家谈起,前门内有个什么庵里的姑子,现在很有势力,并且有一位公主拜在他门下为徒。老人家说过他的名字,我一时记不清楚。这姑子常常到里头去,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上头总说他们出家人以慈悲为主,方便为门,他们来说什么,总得比大概要赏他们一个脸。其实这姑子也是非钱不应的。不过走他的门路,比大概总要近便些。譬如别人要二十万,到他十万也就好了;人家要十万,到他五万也就好了。只要认得了他,是一个冤枉钱不会花的。倘若不认得他,再要别人经手,那就花的大了。”
黄胖姑一听这话,心上毕拍一跳,心想:“被他晓得了这条门路,我的买卖就不成了!”其实黄胖姑心上很晓得这个姑子的来历,而且同他也有往来,因为想赚贾大少爷的钱,只得装作不知。又假意说道:“大爷你既有这条门路,那是顶近便没有了,为什么不去找找他呢?”贾大少爷道:“动身的时候原问过老人家。老人家说:‘你一到京打听人家,像他这样大名鼎鼎,还怕有不晓得的。’所以我来问你,到底他如今怎么样?”黄胖姑假作踌躇道:“你这问可把我问住了。不是我说句大话,北京城里上下三等,九流三教,只要些微有点名气的人,谁不认得我黄胖姑?倒没听说有什么姑子同里头来往。你不要记错,不是姑子,是和尚、道士罢?”贾大少爷道:“的的确确是姑子。老人家说过,我忘记了。”说罢,甚是懊悔。黄胖姑道:“既然说是住在前门里头,你何妨去找找,有了这条门路,也省得东奔西波。咱们是自己人,我也帮着替你打听打听。”贾大少爷道:“如此,费心得很!”坐了一回,又抽了两袋烟,姑娘出条子还没有回来。贾大少爷摸出表来一看,说:“天不早了,我们回去罢。”赛金花始终也没有见面,只有几个老妈送了出来。二人一拱手,各自上车而去。
贾大少爷回到寓处,一宵无话。到了次日,仍旧出门拜客,顺便去访问他老人家所说的那个姑子。一连问了几个朋友,也有略知一二的,也有丝毫不知的。只因这些朋友不是穷京官,就是流寓在京的,一向无事同这姑子往来,难怪他们不晓得,弄得贾大少爷甚为闷闷。一心思想:“我若是把各式事情交托黄胖姑,原无不可;但是经了他手,其中必有几个转折,未免要花冤钱。倘若我找着这个姑子,托他经手一定事半功倍,老人家总不会给我当上的。只恨动身的匆忙,未曾问得仔细,只好慢慢的寻找。”一个人坐在车中往来盘算。一走走到他老人家拜把子的一个都老爷家。这都老爷姓胡名周,为人甚是四海。见了面,居然以世侄相待,问长问短,甚为关切。贾大少爷急不待择,言谈之间,讲及朝政,不说自己想走门路,但说:“如今里头的情形,竟其江河日下了!听说什么当姑子的胆敢出入权门,替人关说,这还了得!”胡都老爷道:“是啊,越是他们出家人,里头越相信。时事如此,无法挽回,也只得付之一叹的了。”贾大少爷道:“老世伯现居言职,何不具折纠参,那倒是名传不朽的。想是不晓得那个庵里的姑子叫个什么名字,所以未曾动手?”胡都老爷道:“名字倒有点晓得,不过现在里头阉寺当权,都成了他们的世界,说了非但无益,反怕贾祸,所以兄弟只得谨守金人之箴,不敢多事。”贾大少爷道:“老世伯身居台谏尚然如此见机,无怪乎朝政日非了。现在京城地面既有这种人,倒不可不请教请教他的名字,将来当作一件新闻谈谈亦好。”胡都老爷想了一回,说道:“这姑子的名字叫镜空。这种人你找他去做啥?如果一定要找他访问个实在,你只要进了前门,沿城脚去问,有几个转弯,我听人家说过,如今也记不得了。”
贾大少爷问到了地方名字,心中暗暗欢喜。同老世伯无甚说得,只得兴辞出来。一见天色尚早,就命车夫替他把车赶进前门。车夫请示进前门到那一家拜客。贾大少爷便按胡都老爷的话,一一告诉了车夫。车夫道声“晓得”,于是把鞭子一洒,展起双轮,不多一刻,捱进前门。约摸转了七八个弯,到得一个所在。只见一道红墙,门前有几棵合抱的大槐树,山门上悬挂着一方匾额,上写“文殊道院”四个大字。山门紧闭不开,却从左首一个侧门内出入。但是门前甚是冷清,并无车马的踪迹。贾大少爷下得车来,车夫在前引路,把他领进了门,乃是一个小小院落,当头一个藤萝架,其时绿叶正茂,赛如搭的凉棚一般,不见天日。院之西面,另有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大殿的院子了。南面三间,开出去便是山门,北面为大殿,左为客堂,右为观音殿,一共是十二间。院子里上首两个砖砌的花台,下首两棵龙爪槐。房子虽不大,倒也清静幽雅。
贾大少爷一路观看,踱进客堂,就有执事的道婆前来打个问讯。贾大少爷便说是专诚来拜镜空师父的。道婆道:“老爷请坐,等我进去通报。”不到一刻,只见道婆引了一个老年尼姑出来。老尼见了贾大少爷,两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动问:“老爷贵姓?是什么风吹到此地?”贾大少爷便把自己的姓名、履历背了几句,又道:“是进京引见,久仰师傅大名,所以特来拜访。”老尼一听他是道台,不觉肃然起敬,连称:“不知大人光降,亵渎得很!……”贾大少爷回称:“说那里话!”又问:“师傅出家几年?是几时到的京城?这庵里香火必盛,来往的人可多?”老尼道:“不瞒大人说,老身原是本京人,出家就在这庵里。是二十五岁上削的发,今年六十五岁了。京城地面乃是红尘世界,老身师徒三众一直是清修,所以这庵里除掉几位施主家的太太、小姐前来做佛事,吃顿把素斋,此外并无杂人来往。大人今天忽然下降,乃是难得之事。”贾大少爷一听不对,沉吟了一会,便问:“师傅的法号,上一个字可是‘水月镜花’的‘镜’字,下一个字可是‘四大皆空’的‘空’字?”老尼道:“下一字不错,上一字乃是‘清静’的‘静’字,并不是‘镜子’的‘镜’字。”贾大少爷便知其中必有错误,忙问:“有位与师傅名字同音的,但是换了一个‘镜’字,这人师傅可认得?”老尼道:“一个北京城,几十里地面,庵观寺院,不计其数,那里一一都能认得。”贾大少爷知道走错了路,只得说了些闲话,搭讪着辞了出来。老尼又要留吃素面。贾大少爷随手在身上摸了一锭银子送与老尼,作为香金,方才拱手出门,匆匆上车而去。
贾大少爷一面上车,一面问车夫道:“不对啊,你从那儿认得这姑子的?”车夫道:“小的从前伺候过顺治门外南横街户部谢老爷,跟着谢老爷来过两趟,所以才认得的。他庵里很有两个年轻的姑子,长的很俊。谢老爷上年在这里请过客,小姑子出来陪着一块儿吃酒。今天想是为着老爷头一趟来,所以小的不出来陪。这庵里很靠不住。”贾大少爷听说,心上一动,把头伸到车子外头往后一瞧,只见刚才替他通报的那个道婆在那里探头探脑的望。此时贾大少爷弄得六神无主,意思想要出城,因听了车夫的话,想要会会那年轻的姑子;待要下车,又见天色渐晚,恐怕赶不出城。车夫见他踌躇,也就停鞭以待。贾大少爷沉吟了一会,道:“今天镜空会不着,倒想不着走到这们一个好地方来。姑且回去通知了黄胖姑,过天同他一块来。他在京里久了,人家不敢欺负他。什么相公、婊子,我都玩过的了,倒要请教请教这尼姑的风味。”说罢,便命车夫赶车出城,过天再来。车夫遵谕,鞭子一洒,骡子已得得而去。贾大少爷又不住的把头伸出来往后探望,一直等到转过弯方才缩进。霎时到得寓所,下车宽衣。只见管家拿了两副帖子上来,当中还夹着一封信。贾大少爷看那帖子,是一副黑伯果,请在致美斋吃午饭;一副是溥四爷,请在他叫的相公顺泉家吃夜饭,都是明日的日期。另外那封信,乃是黄胖姑给他的。贾大少爷看得一半,不觉脸上的颜色改变,等到看完,这一吓更非同小可!欲知信中所言何事,以及贾大少爷明天曾否赴黑、溥二人之约,并后来曾否再去访那姑子,且听下回分解。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