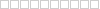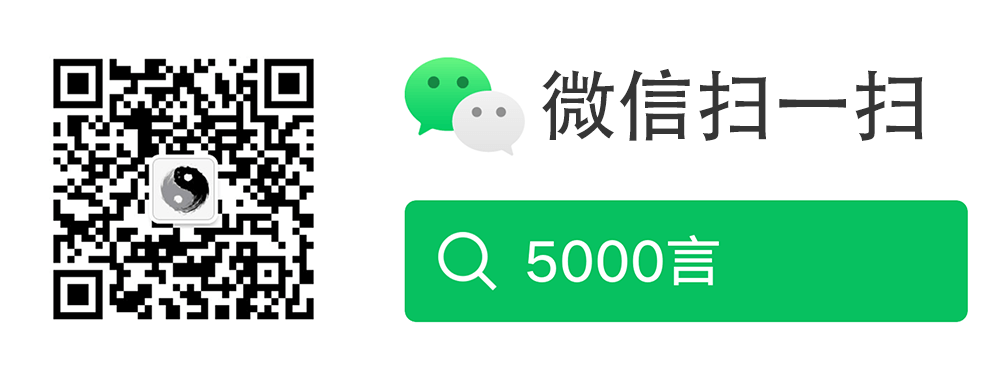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那丫头掀帘出去,便听得有人问道:“赵老爷在这里么?”丫头答应在,那人便掀帘进来。抬头看时,却是方佚庐。大家起身招呼。只见他吃的满面通红,对众人拱一拱手,走到席边一看,呵呵大笑道:“你们整整齐齐的摆在这里,莫非是摆来看的?不然,何以热炒盘子,也不动一动呢?”小云便叫取凳子让他坐。佚庐道:“我不是赴席的,是来请客的,请你们各位一同去。”小云道:“是你请客?”佚庐道:“不是我请,是代邀的。”小云在身边取出表来一看,吐出舌头道:“三下一刻了。是你请客,我便去,你代邀的,我便少陪了。”月卿插嘴道:“便是方老爷也可以不必去了。外面西北风大得很,天已阴下来,提防下雪。并且各位的酒都不少了,到外面去吹了风,不是玩的。”佚庐道:“果然。我方才在外面走动,很作了几个恶心,头脑子生疼,到了屋里,暖和多了。”说着便坐下,叫拿纸笔来写个条子回了那边,只说寻不着朋友,自己也醉了,要回去了。写毕,叫外场送去。方才和采卿招呼,彼此通过姓名。坐了一会,便散席。
月卿道:“此刻天要快亮了,外面寒气逼人,各位不如就在这里谈谈,等天亮了去,或者要睡,床榻被窝都是现成的。”众人或说走,或说不走,都无一定。只有柳采卿住在城里,此时叫城门不便,准定不能走的。便说道:“不然,我再请一席,就可以吃到天亮了。”小云道:“这又何苦呢!方才已经上了一回供了,难道再要上一回么?”月卿道:“那么各位都不要走,我叫他们生一盆炭火来,昨天有人送给我一瓶上好的雨前龙井茶,叫他们酽酽的泡上一壶,我们围炉品茗,消此长夜,岂不好么?”众人听说,便都一齐留下。
佚庐道:“月卿一发做了秀才了,说起话来,总是掉文。”月卿笑道:“这总是识了几个字,看了几本书的不好,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说起来,其实并不是有意的。”小云道:“有一部小说,叫做《花月痕》,你看过么?”月卿道:“看过的。”小云道:“那上头的人,动辄嘴里就念诗,你说他是有意,是无意?”月卿道:“天下那里有这等人,这等事!就是掉文,也不过古人的成句,恰好凑到我这句说话上来,不觉冲口而出的,借来用用罢了。不拘在枕上,在席上,把些陈言老句吟哦起来,偶一为之,倒也罢了,却处处如此,那有这个道理!这部书作的甚好,只这一点是他的疵瑕。”采卿道:“听说这部书是福建人作的,福建人本有这念诗的毛病。”小云忽然呵呵大笑起来。众人忙问他笑什么。小云道:“我才听了月卿说什么疵瑕,心中正在那里想:‘疵瑕者,毛病之文言也。’这又是月卿掉文。不料还没有想完,采翁就说出‘毛病’两个字来,所以好笑。”说话间,丫头早把火盆生好,茶也泡了,一齐送了进来,众人便围炉品茗起来。
佚庐与采卿谈天,采卿又谈起被骗一事。佚庐道:“我们若是早点相识,我断不叫采翁去上这个当。你道齐明如是个什么人?他出身是个外国成衣匠,却不以成衣匠为业,行径是个流氓,事业是靠局赌。从前犯了案,在上海县监禁了一年多,出来之后,又被我办过他一回。”采卿道:“办他什么?”佚庐道:“他有一回带了两个合肥口音的人来,说是李中堂家里的帐房,要来定做两艘小轮船,叫我先打了样子看过,再定价钱。这两艘小轮船,有到七八千银子的生意,自然要应酬他,未免请他们吃一两回酒。他们也回请我,却是吃花酒。吃完之后,他们便赌起来,邀我入局。我只推说不会,在旁边观看,见他们输赢很大,还以为他们是豪客。后来见一个输家输的急了,竟拿出庄票来赌,也输了,又在身边掏出金条来。我心里才明白了,这是明明局赌,他们都是通同一气的,要来引我。须知我也是个老江湖,岂肯上你的当?然而单是避了你,我也不为好汉,须给点颜色你看看。当夜局散之后,我便有意说这赌牌九很有趣,他们便又邀我入局。我道:‘今天没有带钱,过天再来。’于是散了。我一想,这两艘小轮船,不必说是不买的了,不过借此好入我的门。但是无端端的要我打那个图样,虽是我自己动手,不费本钱,可是耽搁了我多少事,若是别人请我画起来,最少也要五十两银子。
“我被他们如此玩弄,那里肯甘心。到明天齐明如一个人来了,我便向他要七十两画图银,请他们来看图。明如邀我出去,我只推说有事,一连几天,不会他们。于是齐明如又同了他们来,看过图样,略略谈了一谈船价。我又先向他要这画图钱。齐明如从中答应,说傍晚在一品香吃大菜面交,又约定了是夜开局。我答应了,送了他们去。到了时候,我便到一品香取了他七十两的庄票。看看他们一班人都齐了,我推说还有点小事,去去就来。出来上了马车,到后马路照票,却是真的。连忙回到四马路,先到巡捕房里去。那巡捕头是我向来认得的,我和他说了这班人的行径,叫他捉人。捕头便派了几名包探、巡捕,跟我去捉人。我和那探捕约好,恐怕他们这班人未齐,被他们跑了一个,也不值得,不如等我先上去。好在坐的是靠马路的房间,如果他们人齐了,我掷一个酒杯下来,这边再上去,岂不是好?那探捕答应了,守在门口。我便走了上楼,果然内中少了一个人,问起来,说是取本钱去的。一面让我点菜。俄延了一会,那个人来了,手里提了一个外国皮夹,嘴里嚷道:‘今天如果再输,我便从此戒赌了!’我看见人齐,便悄悄拿了一个玻璃杯,走到栏杆边,轻轻往下一丢,四五名探捕一拥上楼,入到房间,见人便捉。
“我一同到了捕房,做了原告。在他们身边,搜出了不少的假票子、假金条。捕头对我说:‘这些假东西,告他们骗则可以,告他赌,可没有凭据。’说时,恰好在那皮夹里搜出两颗象牙骰子。我道:‘这便是赌具。’捕头看了看,问怎么赌法。我道:‘单拿这个赌还不算骗人,我还可以在他这里拿出骗人的凭据。’捕头疑讶起来,拿起骰子细看。我道:‘把他打碎了,这里面有铅。’捕头不信。我问他要了个铁锤,把骰子磕碎了一颗,只见一颗又白又亮的东西,骨碌碌滚到地下,却不是铅,是水银。捕头这才信了。这一个案子,两个合肥人办了递解,还有两个办了监禁一年,期满驱逐出境,齐明如侥幸没有在身上搜出东西,只办了个监禁半年。你想这种人结交出什么好外国人来?”
采卿道:“此刻这外国人逃走了,可有什么法子去找他?”佚庐道:“往那里找呢?并且找着了也没用。我们中国的官,见了外国人比老子还怕些,你和他打官司,那里打得赢。”德泉道:“打官司只讲理,管他什么外国人不外国人!”佚庐道:“有那许多理好讲!我前回接了家信,敝省那里有一片公地,共是二十多亩,一向荒弃着没用,却被一个土棍瞒了众人,四两银子一亩,卖给了一个外国人。敝省人最迷信风水,说那片地上不能盖造房子,造了房子,与什么有碍的。所以众人得了这个信息慌了,便往县里去告。提那土棍来问,已经卖绝了,就是办了他,也没用。众人又情愿备了价买转来,那外国人不肯。众人又联名上控,省里派了委员来查办。此时那外国人已经兴工造房子了。那公地旁边,本来有一排二三十家房子,单靠这公地做出路的,他这一造房子,却把出路塞断了,众人越发急了。等那委员到时,都拿了香,环跪在委员老爷跟前,求他设法。”佚庐说到这里,顿住了口道:“你几位猜猜看,这位委员老爷怎么个办法?”众人听得正在高兴,被他这一问,都呆着脸去想那办法。我道:“我们想不出,你快说了罢!”佚庐道:“大凡买了贼赃,明知故买的,是与受同科;不知误买的,应该听凭失主备价取赎。这个法律,只怕是走遍地球,都是一样的了。地棍私卖公地,还不同贼赃一般么?这位委员老爷,才是神明父母呢。他办不下了,却叫人家把那二三十家房子,一齐都卖给了那外国人算完案。”一席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不能赞一词。
佚庐又道:“做官的非但怕外国人,还有一种人,他怕得很有趣的。有一个人为了一件事去告状,官批驳了;再去告,又批驳了。这个人急了,想了个法子,再具个呈子,写的是‘具禀教民某某’。官见了,连忙传审。把这个案判断清楚了之后,官问他:‘你是教民,信的是什么教?’这个人回说道:‘小人信的是孔夫子教。’官倒没奈他何。”说的众人一齐大笑。当下谈谈说说,不觉天亮。月卿叫起下人收拾地方,又招呼吃了点心,众人才散,其时已经九点多钟了。我和德泉走出四马路,只见静悄悄的绝少行人,两旁店铺都没有开门。便回到号里,略睡一睡。是夜便坐了轮船,到南京去。
到家之后,彼此相见,不过都是些家常说话,不必多赘。停顿下来,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看。我接在手里一看,是伯父的信,却从武昌寄来的。看那信上时,说的是王俎香现在湖南办捐局差事,前回借去的三千银子,已经写信托他代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不论双单月的候选通判,统共用了三千二百多两银子,连利钱算上,已经差不多。将来可以到京引见,出来做官,在外面当朋友,终久不是事情云云。又叙上这回到湖北,是两湖总督奏调过去,现在还没有差使。我看完了,倒是一怔。再看那大纸包的是一张监照、一张候选通判的官照,上面还填上个五品衔。我道:“拿着三千多银子,买了两张皮纸,这才无谓呢。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什么?”母亲道:“办个引见,不知再要花多少?就拿这个出去混混也好,总比这跑来跑去的好点。”我道:“继之不在这里,我敢说一句话: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这两件事我都办不到的,怎么好做官!”母亲道:“依你说,继之也卑污苟贱的了?”我道:“怎么好比继之。他遇了前任藩台同他有交情,所以样样顺手。并且继之家里钱多,就是永远没差没缺,他那候补费总是绰绰有余的。我在扬州看见张鼎臣,他那上运司衙门,是底下人背了包裹,托了帽盒子,提了靴子,到官厅上去换衣服的;见了下来,又换了便衣出来。据说这还是好的呢,那比张鼎臣不如的,还要难看呢。”
母亲道:“那么这两张照竟是废的了?”我道:“看着罢,碰个机会,转卖了他。”母亲道:“转卖了,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么?”我道:“这不要紧,只要到部里花上几个钱,可以改的。”母亲道:“虽如此说,但是那个要买,又那个知道你有官出卖?”我道:“自从前两年开了这个山西赈捐,到了此刻,已成了强弩之末,我看不到几时,就要停止的了。到了停止之后,那一班发官迷的,一时捐不及,后来空自懊悔,倘遇了我这个,他还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时,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姊姊从旁笑道:“兄弟近来竟入了生意行了,处处打算赚钱,非但不愿意做官,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我笑道:“我这是退不了的,才打算拿去卖。至于拿官当货物,这个货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卖,我们这个,只好算是‘饭店里买葱’。”当下说笑一回,我仍去料理别的事。
有话便长,无话便短。不知不觉,早又过了新年,转瞬又是元宵佳节,我便料理到汉口去。打听得这天是怡和的上水船。此时怡和、太古两家,南京还没有趸船,只有一家,因官场上落起见,是有的。我便带了行李,到怡和洋篷上去等。等不多时,只见远远的一艘轮船往上水驶来,却是有趸船一家的。暗想今日他家何以也有船来,早知如此,便应该到他那趸船去等,也省了坐划子。正想着时,洋篷里的人也三三两两议论起来。那船也渐驶渐近了,趸船上也扯起了旗子。谁知那船一直上驶,并不停轮。我向来是近视眼,远远的只隐约看见船名上,一个字是三点水旁的,那一个字便看不出了。旁边的人都指手画脚,有人说是这个,有个说是那个,有个说断不是那个,那个字笔画没有那么多。然而为什么一直上驶,并不停轮呢?于是又纷纷议论起来:有个说是恐怕上江那里出了乱事,运兵上去的;有个说是不知专送什么大好老到那里的;有个说怕是因为南京没有客,没有货,所以不停泊的……
大家瞎猜瞎论了一回,早望见红烟囱的元和船到了,在江心停轮。这边的人,纷纷上了划子船,划到轮船边上去。轮船上又下来了多少人。一会便听得一声铃响,船又开行了。我找了一个房舱,放下行李,走出官舱散坐,和一班搭客闲谈。说起有一艘船直放上水的事,各人也都不解。恰好那里买办走来,也说道:“这是向来未曾见过之事,并且开足了快车。我们这元和船,上水一点钟走十二英里,在长江船里,也算头等的快船了。我们在镇江开行,他还没有到,此刻倒被他赶上前头去了。”旁边一个帐房道:“他那个船只怕一点货也不曾装,你不看他轻飘飘的么,船轻了,自然走得快些。但不知到底为了什么事?”当下也是胡猜乱度了一回,各自散开。第三天船到了汉口,我便登岸,到蔡家巷字号里去。一路上只听见汉口的人,三三两两的传说新闻。正是:
直溯长江翻醋浪,谁教平地起酸风?
不知传说什么新闻,且待下回再记。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