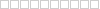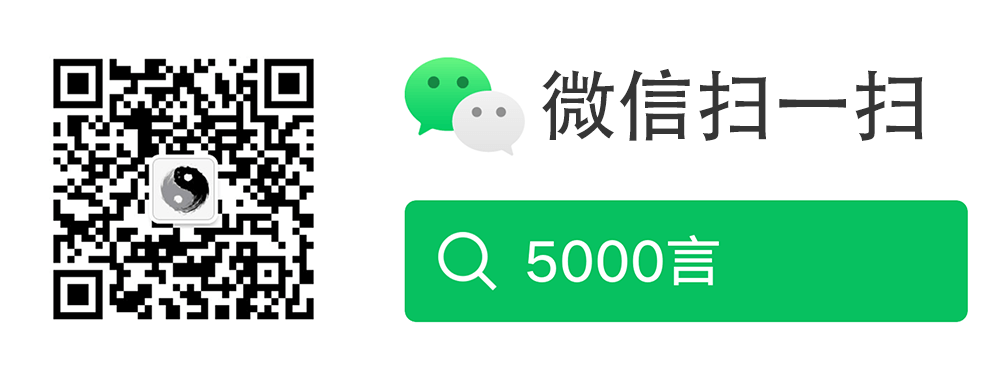第四十卷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诗云:
人生凡事有前期,
尤是功名难强为。
多少英雄埋没杀,
只因莫与指途迷。
话说人生只有科第一事,最是黑暗,没有甚定准的。自古道:“文齐福不齐。”随你胸中锦绣,笔下龙蛇,若是命运不对,倒不如乳臭小儿、卖菜佣早登科甲去了。就如唐时以诗取士,那李、杜、王、孟,不是万世推尊的诗祖?却是李、杜俱不得成进士,孟浩然连官多没有;止有王摩诘一人有科第,又还亏得岐王帮衬,把《郁轮袍》打了九公主关节,才夺得解头。若不会夤缘钻刺,也是不稳的。只这四大家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及至诗不成诗,而今世上不传一首的,当时登第的原不少。看官,你道有甚么清头在那里?所以说:
文章自古无凭据,
惟愿朱衣一点头。
说话的,依你这样说起来,人多不消得读书勤学,只靠着命中福分罢了。看官,不是这话。又道是:“尽其在我,听其在天。”只这些福分,又赶着兴头走的。那奋发不过的人,终久容易得些,也是常理。故此说“皇天不负苦心人”,毕竟水到渠成,应得的多。但是科场中鬼神弄人,只有那该侥幸的时来福凑、该迍邅的七颠八倒,这两项吓死人。先听小子说几件科场中事体,做个起头。
有个该中了,撞着人来帮衬的。湖广有个举人,姓何,在京师中会试。偶入酒肆,见一伙青衣大帽人在肆中饮酒。听他说话,半文半俗;看他气质,假斯文带些光棍腔。何举人另在一座,自斟自酌。这些人见他独自一个寂寞,便来邀他同坐。何举人不辞,就便随和欢畅。这些人道是不做腔,肯入队,且又好相与,尽多快活。吃罢散去。隔了几日,何举人在长安街过,只见一人醉卧路旁,衣帽多被尘土染污。仔细一看,却认得是前日酒肆里同吃酒的内中一人。也是何举人忠厚处,见他醉后狼藉不像样,走近身扶起他来。其人也有些醒了,张目一看,见是何举人扶他,把手拍一拍臂膊,哈哈笑道:“相公造化到了!”就伸手袖中,解出一条汗巾来。汗中结里,裹着一个两指大的小封儿,对何举人道:“可拿到下处自看。”何举人不知其意,袖了到下处去。下处有好几位同会试的在那里,何举人也不道是甚么机密勾当,不以为意,竟在众人面前拆开。看时,乃是六个《四书》题目,八个经题目,共十四个。同寓人见了,问道:“此自何来?”何举人把前日酒肆同饮,今日跌倒街上的话,说了一遍,道:“是这个人与我的,我也不知何来。”同寓人道:“这是光棍们假作此等哄人的,不要信他。”独有一个姓安的心里道:“便是假的何妨?我们落得做做熟也好。”就与何举人约了,每题各做一篇,又在书坊中寻刻的好文,参酌改定。后来入场,六个题目都在这里面的。二人多是预先做下的文字,皆得登第。原来这个醉卧的人,乃是大主考的书办,在他书房中抄得这张题目,乃是一正一副在内。朦胧醉中,见了何举人扶他,喜欢,与了他。也是他机缘辐辏,又挈带了一个姓安的。这些同寓不信的人,可不是命里不该,当面错过?
醉卧者人,吐露者神。
信与不信,命从此分。
有个该中了,撞着鬼来帮衬的。扬州兴化县举子应应天乡试,头场日齁睡,一日不醒。号军叫他起来,日已晚了。正自心慌,且到号底厕上走走。只见厕中已有一个举子在里头,问兴化举子道:“兄文成未?”答道:“正因睡了失觉,一字未成,了不得在这里。”厕中举子道:“吾文皆成,写在王讳纸上,今疾作,誊不得了,兄文既未有,吾当赠兄罢。他日中了,可谢我百金。”兴化举子不胜之喜。厕中举子就把一张王讳纸递过来,果然七篇多明明白白写完在上面,说道:“小弟姓某名某,是应天府学,家在僻乡。城中有卖柴牙人某人,是我侄,可一访之,便可寻我家了。”兴化举子领诺,拿到号房,照他写的誊了,得以完卷。进过三场,揭晓果中。急持百金,往寻卖柴牙人,问他叔子家里。那牙人道:“有个叔子,上科正患痢疾进场,死在场中了。今科那得还有一个叔子?”举子大骇,晓得是鬼来帮他中的。同了牙人,直到他家,将百金为谢。其家甚贫,梦里也不料有此百金之得,阖家大喜。这举子只当百金买了一个春元。
一点文心,至死不磨。
上科之鬼,能助今科。
有个该中了,撞着神借人来帮衬的。宁波有两生,同在鉴湖育王寺读书。一生儇巧,一生拙诚。那拙的信佛,每早晚必焚香在大士座前祷告,愿求明示场中七题。那巧的见他匍匐不休,心中笑他痴呆,思量要耍他一耍,遂将一张大纸,自拟了七题,把佛香烧成字,放在香几下。拙的明日早起拜神,看见了,大信,道是大士有灵,果然密授秘妙。依题遍采坊刻佳文,名友窗课,模拟成七篇好文,熟记不忘。巧的见他信以为实,如此举动,道是被作弄着了,背地暗笑他着鬼。岂知进到场中,七题一个也不差,一挥而出,竟得中式。这不是大士借那儇巧的手,明把题目与他的?
拙以诚求,巧者为用。
鬼神机权,妙于簸弄。
有个该中了,自己精灵现出帮衬的。湖广乡试日,某公在场阅卷倦了,朦胧打盹。只听得耳畔叹息道:“穷死,穷死!救穷,救穷!”惊醒来,想一想道:“此必是有士子要中的作怪了。”仔细听听,声在一箱中出,伸手取卷,每拾起一卷,耳边低低道:“不是。”如此屡屡,落后一卷,听得耳边道:“正是。”某公看看,文字果好,取中之,其声就止。出榜后,本生来见。某公问道:“场后有何异境?”本生道:“没有。”某公道:“场中甚有影响,生平好讲什么话?”本生道:“门生家寒不堪,在窗下每作一文成,只呼‘穷死’,‘救穷’。以此为常,别无他话。”某公乃言阅卷时耳中所闻如此,说了共相叹异,连本生也不知道怎地起的。这不是自己一念坚切,精灵活现么!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果然勇猛,自有神来。
有个该中了,人与鬼神两相凑巧帮衬的。浙场有个士子,原是少年饱学,走过了好几科,多不得中。落后一科,年纪已长,也不做指望了。幸得有了科举,图进场完故事而已。进场之夜,忽梦见有人对他道:“你今年必中,但不可写一个字在卷上;若写了,就不中了,只可交白卷。”士子醒来道:“这样梦也做得奇,天下有这事么?”不以为意。进场领卷,正要构思下笔,只听得耳边厢又如此说道:“决写不得的!”他心里疑道:“好不作怪!”把题目想了一想,头红面热,一字也忖不来。就暴躁起来道:“都管是又不该中了,所以如此。”闷闷睡去。只见祖、父俱来,吩咐道:“你万万不可写一字,包你得中便了。”醒来叹道:“这怎么解?如此梦魂缠扰,料无佳思,吃苦做甚么!落得不做,投了白卷出去罢。”出了场来。自道头一个就是他贴出,不许进二场了。只见试院开门,贴出许多不合式的来,有不完篇的,有脱了稿的,有差写题目的,纷纷不计其数。正拣他一字没有的,不在其内,倒哈哈大笑道:“这些弥封对读的,多失了魂了!”隔了两日,不见动静。随众又进二场,也只是见不贴出,瞒生人眼,进去戏耍罢了。才捏得笔,耳边又如此说。他自笑道:“不劳吩咐,头场白卷,二场写他则甚?世间也没这样呆子。”游衍了半日,交卷而出。道:“这番决难逃了。”只见第二场又贴出许多,仍复没有己名,自家也好生咤异。又随众进了三场,又交了白卷,自不必说。朋友们见他进过三场,多来请教文字,他只好背地暗笑,不好说得。到得榜发,公然榜上有名高中了。他只当是个梦,全不知是那里起的。随着赴鹿鸣宴风骚,真是十分侥幸。领出卷来看,三场俱完好,且是锦绣满纸,惊得目睁口呆,不知其故。原来弥封所两个进士知县,多是少年科第,有意思的,道是不进得内帘,心中不伏气。见了题目,有些技痒,要做一卷试试手段,看还中得与否,只苦没个用印卷子。虽有个把不完卷的,递将上来,却也有一篇半篇先写在上了,用不着的。已后得了此白卷,心中大喜,他两个记着姓名,便你一篇,我一篇,共相斟酌改订,凑成好卷,弥封了,发去誊录。三场皆如此,果然中了出来。两个进士暗地得意,道是“这人有天生造化”,反着人寻将他来,问其白卷之故。此生把梦寐叮嘱之事,场中耳畔之言,一一说了。两个进士道:“我两人偶然之兴,皆是天教代足下执笔的。”此生感激无尽,认做了相知门生。
张公吃酒,李公却醉。
命若该时,一字不费。
这多是该中的话了。若是不该中,也会千奇万怪起来。有一个不该中,鬼神反来耍他的。万历癸未年,有个举人管九皋,赴会试。场前梦见神人传示七个题目,醒来个个记得,第二日寻坊间文,拣好的熟记了。入场七题皆合,喜不自胜。信笔将所熟文字写完,不劳思索。自道是得了神助,心中无疑。谁知是年主考厌薄时文,尽搜括坊间同题文字,入内磨对,有试卷相同的,便涂坏了。管君为此竟不得中,只得选了官去。若非先梦七题,自家出手去做,还未见得不好。这不是鬼神明明耍他?
梦是先机,番成悔气。
鬼善揶揄,直同儿戏。
有一个不该中强中了,鬼神来摆布他的。浙江山阴士人诸葛一鸣,在本处山中发愤读书,不回过岁。隆庆庚午年元旦,未晓,起身梳洗,将往神祠中祷祈。途间遇一群人,喝道而来。心里疑道:“山中安得有此?”伫立在旁细看,只见鼓吹前导,马上簇拥着一件东西。落后贵人到,乃一金甲神也。一鸣明知是阴间神道,迎上前来。拜问道:“尊神前驱所迎何物?”神道:“今科举子榜。”一鸣道:“小生某人,正是秀才,榜上有名否?”神道:“没有。君名在下科榜上。”一鸣道:“小生家贫,等不得。尊神可移早一科否?”神道:“事甚难。然与君相遇,亦有缘,试为君图之。若得中,须多焚楮钱,我要去使用才安稳。不然,我亦有罪犯。”一鸣许诺。及后边榜发,一鸣名在末行,上有丹印。缘是数已填满,一个教官将着一鸣卷竭力来荐,至见诸声色。主者不得已,割去榜末一名,将一鸣填补。此是鬼神在暗中作用。一鸣得中甚喜,匆匆忘了烧楮钱。赴宴归寓,见一鬼披发,在马前哭道:“我为你受祸了。”一鸣认看,正是先前金甲神。甚不过意,道:“不知还可焚钱相救否?”鬼道:“事已迟了,还可相助。”一鸣买些楮钱烧了。及到会试,鬼复来道:“我能助公登第,预报七题。”一鸣打点了进去,果然不差。一鸣大喜。到第二场,将到进去了,鬼才来报题。一鸣道:“来不及了。”鬼道:“将文字放在头巾内带了进去,我遮护你便了。”一鸣依了他。到得监试面前,不消搜得,巾中文早已坠下。算个怀挟作弊,当时打了枷号示众,前程削夺。此乃鬼来报前怨,作弄他的。可见命未该中,只早一科也是强不得的。
躁于求售,并丧厥有。
人耶鬼耶?各任其咎。
看官,只看小子说这几端,可见功名定数,毫不可强。所以道:
窗下莫言命,场中不论文。
世间人总在这定数内,被他哄得昏头昏脑的。小子而今说一段指破功名定数的故事来,完这回正话。
唐时有个江陵副使李君。他少年未第时,自洛阳赴长安进士举,经过华阴道中,下店歇宿。只见先有一个白衣人在店。虽然浑身布素,却是骨秀神清,丰格出众。店中人甚多,也不把他放在心上。李君是个聪明有才思的人,便瞧科在眼里道:“此人决然非凡。”就把坐来移近了,把两句话来请问他,只见谈吐如流,百叩百应。李君愈加敬重,与他围炉同饮,款洽倍常。明日一路同行,至昭应。李君道:“小弟慕足下尘外高踪,意欲结为兄弟。倘蒙不弃,伏乞见教姓名年岁,以便称呼。”白衣人道:“我无姓名,亦无年岁。你以兄称我,以兄礼事我可也。”李君依言,当下结拜为兄。至晚,对李君道:“我隐居西岳,偶出游行,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我有事故,明旦先要往城,不得奉陪如何?”李君道:“邂逅幸与高贤结契,今遽相别,不识有甚言语指教小弟否?”白衣人道:“郎君莫不要知后来事否?”李君再拜,恳请道:“若得预知后来事,足可趋避,省得在黑暗中行,不胜至愿。”白衣人道:“仙机不可泄漏,吾当缄封三书与郎君,日后自有应验。”李君道:“所以奉恳,专贵在先知后事。若直待事后有验,要晓得他怎的?”白衣人道:“不如此说。凡人功名富贵,虽自有定数,但吾能前知,便可为郎君指引。若到其间开他,自身用处,可以周全郎君富贵。”李君见说,欣然请教。白衣人乃取纸笔,在月下不知写些甚么,折做三个柬,外用三个封封了。拿来交与李君,道:“此三封,郎君一生要紧事体在内。封有次第,内中有秘语,直到至急时,方可依次而开。开后自有应验。依着做去,当得便宜。若无急事,漫自开他,一毫无益的。切记!切记!”李君再拜领受,珍藏箧中。次日各相别去。
李君到了长安,应过进士举,不得中第。李君父亲在时,是松滋令,家事颇饶。只因带了宦囊到京营求升迁,病死客邸,宦囊一空。李君痛父沦丧,门户萧条,意欲中第才归,重整门阀。家中多带盘缠,拼住京师,不中不休。自恃才高,道是举手可得,如拾芥之易。怎知命运不对,连应过五六举,只是下第,盘缠多用尽了。欲待归去,无有路费。欲待住下以俟再举,没了赁房之资,求容足之地也无。左难右难,没个是处。正在焦急头上,猛然想道:“仙兄有书,吩咐道有急方开。今日已是穷极无聊,此不为急,还要急到那里去?不免开他头一封,看是如何。然是仙书,不可造次。”是夜沐浴斋素。到第二日清旦,焚香一炉,再拜祷告道:“弟子只因穷困,敢开仙兄第一封书,只望明指迷途则个。”告罢,拆开外封,里面又有一小封。面上写着道:
某年月日,以困迫无资用,开第一封。
李君大惊道:“真神仙也!如何就晓得今日目前光景?且开封的月日,俱不差一毫。可见正该开的,内中必有奇处。”就拆开小封来看,封内另有一纸,写着不多几个字:
可青龙寺门前坐。
看罢,晓得有些奇怪,怎敢不依?只是疑心道:“到那里去何干?”问问青龙寺远近,原来离住处有五十多里路。李君只得骑了一头蹇驴,迍迍走到寺前,日色已将晚了。果然依着书中言语,在门槛上呆呆地坐了一回,不见甚么动静。天昏黑下来,心里有些着急,又想了仙书,自家好笑道:“好痴子!这里坐,可是有得钱来的么?不指望钱,今夜且没讨宿处了。怎么处?”正迟疑间,只见寺中有人行走响。看看至近,却是寺中主僧和个行者来关前门。见了李君,问道:“客是何人,坐在此间?”李君道:“驴弱居远,天色已晚,前去不得,将寄宿于此。”主僧道:“门外风寒,岂是宿处?且请到院中来。”李君推托道:“造次不敢惊动。”主僧再三邀进,只得牵了蹇驴,随着进来。主僧见是士人,具馔烹茶,不敢怠慢。饮间,主僧熟视李君,上上下下估着。看了一回,就转头去与行童说一番,笑一番。李君不解其意,又不好问得。只见主僧耐了一回,突然问道:“郎君何姓?”李君道:“姓李。”主僧惊道:“果然姓李!”李君道:“见说贱姓,如此着惊何故?”主僧道:“松滋李长官,是郎君盛族,相识否?”李君站起身,颦蹙道:“正是某先人也。”主僧不觉垂泪不已,说道:“老僧与令先翁长官,久托故旧,往还不薄。适见郎君丰仪酷似长官,所以惊疑。不料果是!老僧奉求已多日,今日得遇,实为万幸。”李君见说着父亲,心下感伤,涕流被面,道:“不晓得老师与先人旧识,顷间造次失礼。然适闻相求弟子已久,不解何故?”主僧道:“长官昔年将钱物到此求官,得疾狼狈。有钱二千贯,寄在老僧常住库中。后来一病不起,此钱无处发付。老僧自是以来,心中常如有重负,不能释然。今得郎君到此,完此公案,老僧此生无事矣。”李君道:“向来但知先人客死,宦囊无迹,不知却寄在老师这里。然此事无个证见,非老师高谊在古人之上,怎肯不昧其事,反加意寻访?重劳记念,此德难忘。”主僧道:“老僧世外之人,要钱何用?何况他人之财,岂可没为己有,自增罪业!老僧只怕受托不终,致负夙债,贻累来生。今幸得了此心事,魂梦皆安。老僧看郎君行况萧条,明日但留下文书一纸,做个执照,尽数辇去为旅邸之资,尽可营生,尊翁长官之目也瞑了。”李君悲喜交集,悲则悲着父亲遗念,喜则喜着顿得多钱。称谢主僧不尽,又自念仙书之验如此,真希有事也。
青龙寺主古人徒,
受托钱财谊不诬。
贫子衣珠虽故在,
若非仙诀可能符?
是晚主僧留住安宿,殷勤相待。次日尽将原镪二千贯发出,交明与李君。李君写个收领文字,遂雇骡驮载,珍重而别。
李君从此买宅长安,顿成富家。李君一向门阀清贵,只因生计无定,连妻子也不娶得。今长安中大家见他富盛起来,又是旧家门望,就有媒人来说亲与他。他娶下成婚,作久住之计。又应过两次举,只是不第,年纪看看长了。亲戚朋友仆从等,多劝他且图一官,以为终身之计,如何被科名骗老了?李君自恃才高,且家有余资,不愁衣食,自道:“只争得此一步,差好多光景。怎肯甘心就住,让那才不如我的得意了,做尽天气!且索再守他次把做处。”本年又应一举,仍复不第,连前却满十次了。心里虽是不伏气,却是递年打毷氉,也觉得不耐烦了。说话的,如何叫得“打毷氉”?看官听说:唐时榜发后,与不第的举子吃解闷酒,浑名“打毷氉”。此样酒席可是吃得十来番起的。李君要住住手,又割舍不得;要宽心再等,不但撺掇的人多,自家也觉争气不出了。况且妻子又未免图他一官半职荣贵,耳边日常把些不入机的话来激聒。一发不知怎地好,竟自没了主意。含着一眶眼泪道:“一歇了手,终身是个不第举子。就侥幸官职高贵,也说不响了。”踌躇不定几时,猛然想道:“我仙兄有书道急时可开。此时虽无非常急事,却是住与不住,是我一生了当的事,关头所差不小。何不开他第二封一看,以为行止。”生意定了,又斋戒沐浴。次日清旦,启开外封,只见里面写道:
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开第二封。
李君大喜道:“原来原该是今日开的。既然开得不差,里面必有决断,吾终身可定了。”忙又开了小封看时,也不多几个字,写着:
可西市鞦辔行头坐。
李君看了道:“这又怎么解?我只道明明说个还该应举不应举,却又是哑谜。当日青龙寺,须有个寺僧欠钱;这个西市鞦辔行头,难道有人欠我及第的债不成?但是仙兄说话不曾差了一些,只索依他走去,看是甚么缘故。却其实有些好笑。”自言自语了一回,只得依言,一直走去。走到那里,自想道:“可在那处坐好?”一眼望去,一个去处,但见:
望子高挑,埕头广架。门前对子,强斯文带醉歪题;壁上诗篇,村过客乘忙诌下。入门一阵腥膻气,案上原少佳肴;到坐几番吆喝声,面前未来供馔。谩说闻香须下马,枉夸知味且停骖。无非行路救饥,或是邀人议事。
原来是一个大酒店。李君独坐无聊,想道:“我且沽一壶吃着坐看。”步进店来。店主人见是个士人,便拱道:“楼上有洁净坐头,请官人上楼去。”李君上楼坐定。看那楼上的东首尽处,有间洁净小阁子,门儿掩着。像有人在里边坐下的,寂寂默默在里头。李君这付座底下,却是店主人的房,楼板上有个穿眼,眼里偷窥下去,是直见的。李君一个在楼上,还未见小二送酒菜上来。独坐着闲不过,听得脚底下房里头低低说话,他却在地板眼里张看。只见一个人将要走动身,一个拍着肩叮嘱,听得落尾两句说道:“教他家郎君明日平明,必要到此相会。若是苦没有钱,即说原是且未要钱的。不要错过,迟一日就无及了。”去的那人道:“他还疑心不的确,未肯就来,怎好?”李君听得这几句话有些古怪,便想道:“仙兄之言莫非应着此间人的事体么?”即忙奔下楼来,却好与那两个人撞个劈面,乃是店主人与一个陌生人。李君扯住店主人问道:“你们适才讲的是甚么话?”店主人道:“侍郎的郎君,有件紧要事干,要一千贯钱来用,托某等寻觅,故此商量寻个头主。”李君道:“一千贯钱,不是小事,那里来这个大财主好借用?”店主道:“不是借用,说得事成时,竟要了他这一千贯钱也还算是相应的。”李君再三要问其事备细。店主人道:“与你何干!何必定要说破?”只见那要去的人立定了脚,看他问得急切,回身来道:“何不把实话对他说?总是那边未见得成,或者另绊得头主,大家商量商量也好。”店主人方才附着李君耳朵说道:“是营谋来岁及第的事。”李君正斗着肚子里事,又合着仙兄之机,吃了一惊。忙问道:“此事虚实何如?”店主人道:“侍郎郎君,见在楼上房内,怎的不实?”李君道:“方才听见你们说话,还是要去寻那个的是?”店主人道:“有个举人要做此事,约定昨日来成的,直等到晚,竟不见来。不知为凑钱不起,不知为疑心不真。却是郎君原未要钱,直等及第了才交足。只怕他为无钱不来,故此又要这位做事的朋友去约他。若明日不来,郎君便自去了,只可惜了这好机会。”李君道:“好教两位得知,某也是举人。要钱时某也有。便就等某见一见郎君,做了此事,可使得否?”店主人道:“官人是实话么?”李君道:“怎么不实?”店主人道:“这事原不拣人的。若实实要做,有何不可?”那个人道:“从古道‘有奶便为娘’,我们见钟不打,倒去敛铜?官人若果要做,我也不到那边去,再走坏这样闲步了。”店主人道:“既如此,可就请上楼,与郎君相见面议何如?”两个人拉了李君,一同走到楼上来。
那个人走去东首阁子里,说了一会话。只见一个人踱将出来,看他怎生模样:
白胖面庞,痴肥身体。行动许多珍重,周旋颇少谦恭。抬眼看人,常带几分蒙昧;出言对众,时牵数字含糊。顶着祖父现成家,享这儿孙自在福。
这人走出阁来,店主人忙引李君上前,指与李君道:“此侍郎郎君也,可小心拜见。”李君施礼已毕,叙坐了。郎君举手道:“公是举子么?”李君通了姓名,道:“适才店主人所说来岁之事,万望扶持。”郎君点头未答,且目视店主人与那个人,做个手势道:“此话如何?”店主人道:“数目已经讲过,昨有个人约着不来,推道无钱。今此间李官人有钱,情愿成约。故此,特地引他谒见郎君。”郎君道:“咱要钱不多,如何今日才有主?”店主人道:“举子多贫,一时间斗不着。”郎君道:“拣那富的拉一个来罢了。”店主人道:“富的要是要,又撞不见这样方便。”郎君又拱着李君问店主人道:“此间如何?”李君不等店主人回话,便道:“某寄籍长安,家业多在此,只求事成,千贯易处,不敢相负。”郎君道:“甚妙!甚妙!明年主司侍郎,乃吾亲叔父也,也不误先辈之事。今日也未就要交钱,只立一约,待及第之后,即命这边主人走领,料也不怕少了的。”李君见说得有根因,又且是应着仙书,晓得其事必成,放胆做着,再无疑虑。即袖中取出两贯钱来,央店主人备酒来吃。一面饮酒,一面立约,只等来年成事交银。当下李君又将两贯钱谢了店主人与那一个人,各各欢喜而别。到明年应举,李君果得这个关节之力,榜下及第。及第后,将着一千贯完那前约,自不必说。眼见得仙兄第二封书,指点成了他一生之事。
真才屡挫误前程,
不若黄金立可成。
今看仙书能指引,
方知铜臭亦天生。
李君得第授官。自念富贵功名,皆出仙兄秘授谜诀之力。思欲会见一面,以谢恩德,又要细问终身之事。差人到了华阴西岳,各处探访,并无一个晓得这白衣人的下落,只得罢了。以后仕宦得意,并无甚么急事可问,这第三封书无因得开。官至江陵副使,在任时,一日忽患心痛,少顷之间,晕绝了数次,危迫特甚。方转念起第三封书来,对妻子道:“今日性命俄顷,可谓至急。仙兄第三封书可以开看,必然有救法在内了。”自己起床不得,就叫妻子灌洗了,虔诚代开。开了外封,也是与前两番一样的家数,写在里面道:
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开第三封。
妻子也喜道:“不要说时日相合,连病多晓得在先了,毕竟有解救之法。”连忙开了小封,急急看时,只叫得苦。原来比先前两封的字越少了,刚刚止得五字道:
可处置家事。
妻子看罢,晓得不济事了,放声大哭。李君笑道:“仙兄数已定矣,哭他何干?吾贫,仙兄能指点富吾;吾贱,仙兄能指点贵吾;今吾死,仙兄岂不能指点活吾?盖因是数,去不得了。就是当初富吾、贵吾,也原是吾命中所有之物。前数分明,止是仙兄前知,费得一番引路。我今思之:一生应举,真才却不能一第,直待时节到来,还要遇巧假手于人,方得成名,可不是数已前定?天下事大约强求不得的。而今官位至此,仙兄判断已决,我岂复不知止足,尚怀遗恨哉?”遂将家事一面处置了当。隔两日,含笑而卒。
这回书叫作《三拆仙书》,奉劝世人看取:数皆前定如此,不必多生妄想。那有才不遇时之人,也只索引命自安,不必抑郁不快了。
人生自合有穷时,
纵是仙家讵得私?
富贵只缘乘巧凑,
应知难改盖棺期。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