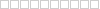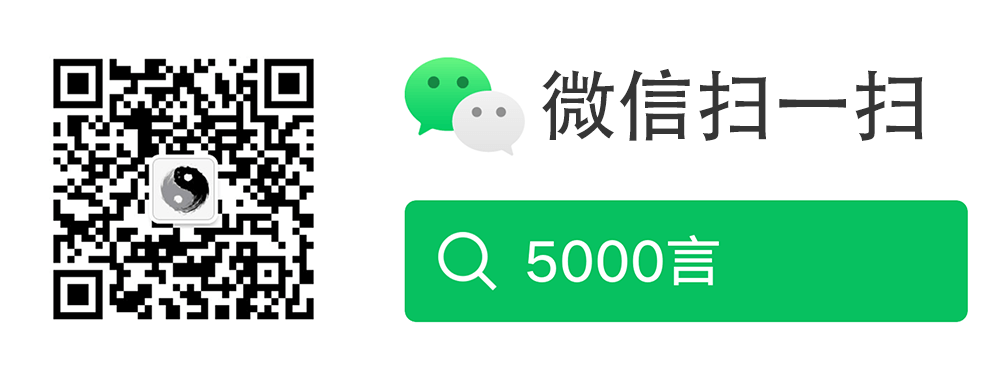第三十卷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诗曰:
冤业相报,自古有之。
一作一受,天地无私。
杀人还杀,自刃何疑?
有如不信,听取谈资。
话说天地间,最重的是生命。佛说戒杀,还说杀一物要填还一命。何况同是生人,欺心故杀,岂得不报?所以律法上最严杀人偿命之条。汉高祖除秦苛法,止留下三章,尚且头一句,就是“杀人者死”,可见杀人罪极重。但阳世间不曾败露,无人知道,那里正得许多法?尽有漏了网的,却不那死的人落得一死了?所以就有阴报。那阴报事也尽多,却是在幽冥地府之中,虽是分毫不爽,无人看见。就有人死而复苏,传说得出来。那口强心狠的人,只认做说的是梦话,自己不曾经见,那里肯个个听?却有一等,即在阳间受着再生冤家现世花报的,事迹显著,明载史传,难道也不足信?还要口强心狠哩!在下而今不说那彭生惊齐襄公,赵王如意赶吕太后,窦婴、灌夫鞭田蚡,这还是道“时衰鬼弄人”,又道是“疑心生暗鬼”,未必不是阳命将绝,自家心上的事发,眼花缭花上头起来的。只说些明明白白的现世报,但是报法有不同。看官不嫌絮烦,听小子多说一两件,然后入正话。
一件是唐《逸史》上说的。长安城南,曾有僧日中求斋。偶见桑树上有一女子,在那里采桑,合掌问道:“女菩萨,此间侧近何处有信心檀越,可化得一斋的么?”女子用手指道:“去此三四里,有个王家,见在设斋之际。见和尚来到,必然喜舍,可速去。”僧随他所相处前往。果见一群僧,正要就坐吃斋。此僧来得恰好,甚是喜欢。斋罢,王家翁姥见他来得及时,问道:“师父像个远来的,谁指引到此?”僧道:“三四里外,有个小娘子在那里采桑,是他教导我的。”翁姥大惊道:“我这里设斋,并不曾传将开去。三四里外女子从何知道?必是个未卜先知的异人,非凡女也。”对僧道:“且烦师父与某等同往,访这女子则个。”翁姥就同了此僧,到了那边。那女子还在桑树上。一见了王家翁姥,即便跳下树来,连桑篮丢下了,望前极力奔走。僧人自去了,翁姥随后赶来。女子走到家,自进去了。王翁认得这家,是村人卢叔伦家里,也走进来。女子跑进到房里,掇张床来抵住了门,牢不可开。卢母惊怪他两个老人家赶着女儿,问道:“为甚么?”王翁、王母道:“某今日家内设斋,落末有个远方僧来投斋,说是小娘子指引他的。某家做此功德,并不曾对人说。不知小娘子如何知道,故来问一声,并无甚么别故。”卢母见说,道:“这等打甚么紧,老身去叫他出来。”就走去敲门叫女儿,女儿坚不肯出。卢母大怒道:“这是怎的起?这小奴才作怪了!”女子在房内回言道:“我自不愿见这两个老货,也没甚么罪过。”卢母道:“邻里翁婆看你,有甚不好意思?为何躲着不出?”王翁、王姥见他躲避得紧,一发疑心道:“必有奇异之处。”在门外着实恳求,必要一见。女子在房内大喝道:“某年月日,有贩胡羊的父子三人,今在何处?”王翁、王姥听见说了这句,大惊失色。急急走出,不敢回头一看。恨不得多生两只脚,飞也似的去了。女子方开出门来,卢母问道:“适才的话,是怎么说?”女子道:“好叫母亲得知,儿再世前曾贩羊,从夏州来到此翁姥家里投宿。父子三人尽被他谋死了,劫了资货,在家里受用。儿前生冤气不散,就投他家做了儿子,聪明过人。他两人爱同珍宝。十五岁害病,二十岁死了。他家里前后用过医药之费,已比劫得的多过数倍了。又每年到了亡日,设了斋供,夫妻啼哭,总算他眼泪也出了三石多了。儿今虽生在此处,却多记得前事。偶然见僧化饭,所以指点他。这两个是宿世冤仇,我还要见他怎么?方才提破他心头旧事,吃这一惊不小,回去即死,债也完了。”卢母惊异,打听王翁夫妻,果然到得家里,虽不知这些清头,晓得冤债不了,惊悸恍惚成病,不多时,两个多死了。看官,你道这女儿三生,一生被害,一生索债,一生证明讨命,可不利害么?略听小子胡诌一首诗:
采桑女子实堪奇,
记得为儿索债时。
导引僧家来乞食,
分明追取赴阴司。
这是三生的了。再说个两世的,死过了,鬼来报冤的。这一件,在宋《夷坚志》上。说吴江县二十里外因渎村,有个富人吴泽,曾做个将仕郎,叫作吴将仕。生有一子,小字云郎。自小即聪明勤学,应进士第,预待补籍,父母望他指日峥嵘。绍兴五年八月,一病而亡。父母痛如刀割,竭尽资财替他追荐超度。费了若干东西,心里只是苦痛,思念不已。明年冬,将仕有个兄弟,做助教的,名兹,要到洞庭东山妻家去。未到数里,暴风打船,船行不得,暂泊在福善王庙下,躲过风势。登岸闲步。望庙门半掩,只见庙内一人,着皂绨背子,缓步而出,却像云郎。助教走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正是他,吃了一大惊。明知是鬼魂,却对他道:“你父母晓夜思量你,不知赔了多少眼泪,要会你一面不能勾。你却为何在此?”云郎道:“儿为一事,拘系在此。留连证对,况味极苦。叔叔可为我致此意于二亲,若要相见,须亲自到这里来乃可。我却去不得。”叹息数声而去。助教得此消息,不到妻家去了,急还家来对兄嫂说知此事。三个人大家恸哭了一番,就下了助教这只原船,三人同到底前来。只见云郎已立在水边,见了父母,奔到面前哭拜,具述幽冥中苦恼之状。父母正要问他详细,说自家思念他的苦楚,只见云郎忽然变了面孔,挺竖双眉,捽住父衣,大呼道:“你陷我性命,盗我金帛,使我衔冤茹痛四五十年。虽曾费耗过好些钱,性命却要还我。今日决不饶你!”说罢,便两相击博,滚入水中。助教慌了,喝叫仆从及船上人,多跳下水去捞救。那太湖边人多是会水的,救得上岸。还见将仕指手画脚,挥拳相争。到夜方定。助教不知甚么缘故,却听得适才的说话,分明晓得定然有些蹊跷的阴事,来问将仕。将仕蹙着眉头道:“昔日壬午年间,虏骑破城,一个少年子弟相投寄宿,所赍囊金甚多,吾心贪其所有,数月之后,乘醉杀死,尽取其赀。自念冤债在身,从壮至老,心中长怀不安。此儿生于壬午,定是他冤魂再世,今日之报,已显然了。”自此忧闷不食,十余日而死。这个儿子只是两生。一生被害,一生讨债,却就做了鬼来讨命。比前少了一番,又直捷些。再听小子胡诌一首诗:
冤魂投托原财耗,
落得悲伤作利钱。
儿女死亡何用哭?
须知作业在生前。
这两件事希奇些的说过。至于那本身受害,即时做鬼取命的,就是年初一起,说到年晚除夜,也说不尽许多。小子要说正话,不得工夫了。说话的,为何还有个正话?看官,小子先前说这两个,多是一世再世,心里牢牢记得前生,以此报了冤仇,还不希罕。又有一个再世转来,并不知前生甚么的,遇着各别道路的一个人,没些意思,定要杀他,谁知是前世冤家做定的。天理自然果报,人多猜不出来,报的更为直捷,事儿更为奇幻,听小子表白来。这本话,却在唐朝贞元年间。有一个河朔李生,从少时膂力过人,恃气好侠,不拘细行。常与这些轻薄少年,成群作队,驰马试剑,黑夜里往来太行山道上,不知做些什么不明不白的事。后来家事忽然好了,尽改前非,折节读书,颇善诗歌,有名于时,做了好人了。累官河朔,后至深州录事参军。李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又且廉谨明干,甚为深州太守所知重。至于击鞠、弹棋、博弈诸戏,无不曲尽其妙。又饮量尽大,酒德又好,凡是宴会酒席,没有了他,一坐多没兴。太守喜欢他,真是时刻上不得的。其时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自恃曾为朝廷出力,与李抱真同破朱滔,功劳甚大,又兼兵精马壮,强横无比,不顾法度。属下州郡太守,个个惧怕他威令,心胆俱惊。其子士真,就受武俊之节,官拜副大使。少年骄纵,倚着父亲戚势,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一日,武俊遣他巡行属郡,真个是:
轰天吓地,掣电奔雷。喝水成冰,驱山开路。川岳为之震动,草木尽是披靡。深林虎豹也潜形,村舍犬鸡都不乐。
别郡已过,将次到深州来。太守畏惧武俊,正要奉承得士真欢喜,好效殷勤。预先打听他前边所经过,喜怒行径详悉。闻得别郡多因陪宴的言语举动,每每触犯忌讳,不善承颜顺旨,以致不乐。太守于是大具牛酒,精治肴馔,广备声乐,妻孥手自烹庖,太守躬亲陈设。百样整齐,只等副大使来。只见前驱探马来报,副大使头踏到了。但见:
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开山斧闪烁生光,还带杀人之血;流星锤蓓蕾出色,犹闻磕脑之腥。铁链响琅玱,只等悔气人冲节过;铜铃声杂沓,更无拼死汉逆前来。蹂躏得地上草不生,篙恼得梦中魂也怕。
士真既到,太守郊迎过,请在极大的一所公馆里安歇了。登时酒筵,嗄程礼物,抬将进来。太守恐怕有人触犯,只是自家一人小心陪侍。一应僚吏宾客,一个也不召来与席。士真见他酒者丰美,礼物隆重,又且太守谦恭谨慎,再无一个杂客敢轻到面前,心中大喜。道是经过的各郡,再没有到得这郡齐整谨饬了。饮酒至夜。
士真虽是威严,却是年纪未多,兴趣颇高,饮了半日酒,止得一个太守在面前唯喏趋承,心中虽是喜欢,觉得没些韵味。对太守道:“幸蒙使君雅意,相待如此之厚,欲尽欢于今夕。只是我两人对酌,觉得少些高兴,再得一两个人同酌,助一助酒兴为妙。”太守道:“敝郡偏僻,实少名流。况兼惧副大使之威,恐忤尊旨,岂敢以他客奉陪宴席?”士真道:“饮酒作乐,何所妨碍?况如此名郡,岂无嘉宾?愿得召来,帮我们鼓一鼓兴,可以尽欢。不然,酒伴寂寥,虽是盛筵,也觉吃不畅些。”太守见他说得在行,想道:“别人卤莽不济事。难得他恁地喜欢高兴。不要请个人不凑趣,弄出事来。只有李参军风流蕴藉,且是谨慎,又会言谈戏艺,酒量又好。除非是他,方可中意,我也放得心下。第二个就使不得了。”想了一回,方对士真说道:“此间实少韵人,可以佐副大使酒政。止有录事参军李某,饮量颇洪,兴致亦好。且其人善能诙谐谈笑,广晓技艺,或者可以赐他侍坐,以助副大使雅兴万一。不知可否,未敢自专,仰祈尊裁。”士真道:“使君所幸,必是妙人。召他来看。”太守呼唤从人,“速请李参军来。”看官,若是说话的人那时也在深州地方,与李参军一块儿住着,又有个未卜先知之法,自然拦腰抱住,劈胸楸着,劝他不吃得这样吕太后筵席也罢,叫他不要来了。只因李生闻召,虽是自觉有些精神恍惚,却是副大使的钧旨,本郡太守命令,召他同席,明明是抬举他,怎敢不来?谁知此一去,却似:
猪羊入屠户之家,
一步步来寻死路。
说话的,你差了!无非叫他去帮吃杯酒儿,是个在行的人,难道有甚么言语冲撞了他,闯出祸来不成?看官,你听,若是冲撞了他,惹出祸来,这是本等的事,何足为奇?只为不曾说一句,白白地就送了性命,所以可笑。且待我接上前因,便见分晓。那时,李参军随命而来,登了堂望着士真就拜。拜罢,抬起头来。士真一看,便勃然大怒。既召了来,免不得赐他坐了。李参军勉强坐下,心中悚惧,状貌益加恭谨。士真越看越不快活起来。看他揎拳裸袖,两眼睁得铜铃也似;一些笑颜也没有,一句闲话也不说,却像个怒气填胸,寻事发作的一般,比先前竟似换了一个人了。太守慌得无所措手足,且又不知所谓,只得偷眼来看李参军。但见李参军面如土色,冷汗淋漓,身体颤抖抖的,坐不住。连手里拿的杯盘,也只是战,几乎掉下地来。太守恨不得身子替了李参军,说着句把话,发个甚么喜欢出来便好。争奈一个似鬼使神差,一个似失魂落魄。李参军平日枉自许多风流俏倬,谈笑科分,竟不知撩在爪哇国那里去了。比那泥塑木雕的,多得一味抖。连满堂伏侍的人,都慌得来没头没脑,不敢说一句话,只冷眼瞧他两个光景。只见不多几时,士真像个忍耐不住的模样,忽地叫了一声:“左右那里?”左右一伙人,暴雷也似答应了一声:“喏!”士真吩咐把李参军拿下。左右就在席上如鹰拿雁雀,楸了下来听令。士真道:“且收郡狱!”左右即牵了李参军衣袂,付在狱中,来回话了。士真冷笑了两声,仍旧欢喜起来。照前发兴吃酒,他也不说甚么缘故来。太守也不敢轻问,战战兢兢陪他,酒散,早已天晓了。
太守只这一出,被他惊坏,又恐怕因此惹恼了他,连自家身子立不勾。却又不见得李参军触恼他一些处,正是不知一个头脑。叫着左右伏侍的人,逐个盘问道:“你们旁观仔细,曾看出甚么破绽么?”左右道:“李参军自不曾开一句口,在那里触犯了来?因是众人多疑心这个缘故。却又不知李参军如何便这般惊恐,连身子多主张不住,只是个颤抖抖的。”太守道:“既是这等,除非去问李参军,他自家或者晓得甚么冲撞他处,故此先慌了,也不见得。”太守说罢,密地叫个心腹的祗候人去到狱中,传太守的说话。问李参军道:“昨日的事,参军貌甚恭谨,且不曾出一句话,原没处触犯了副大使。副大使为何如此发怒?又且系参军在狱?参军自家可晓得甚么缘故么?”李参军只是哭泣,把头摇了又摇,只不肯说甚么出来。祗候人又道是奇怪,只得去告诉太守道:“李参军不肯说话,只是一味哭。”太守一发疑心了,道:“他平日何等一个精细爽利的人,今日为何却失张失智到此地位!真是难解。”只得自己走进狱中来问他。他见了太守,想着平日知重之恩,越哭得悲切起来。太守忙问其故。李参军沉吟了半晌,叹了一口气,才拭眼泪说道:“多感君侯惓惓垂问,某有心事,今不敢隐。曾闻释家有现世果报,向道是惑人的说话,今日方知此话不虚了。”太守道:“怎见得?”李参军道:“君侯不要惊怪,某敢尽情相告。某自上贫,无以自资衣食,因恃有几分膂力,好与侠士剑客往来,每每掠夺里人的财帛,以充己用。时常驰马腰弓,往还太行道上,每日走过百来里路,遇着单身客人,便劫了财物归家。一日,遇着一个少年,手执皮鞭,赶着一个骏骡,骡背负着两个大袋。某见他沉重,随了他一路走去。到一个山坳之处,左右岩崖万仞。彼时日色将晚,前无行人,就把他尽力一推,推落崖下,不知死活。因急赶了他这头骏骡,到了下处,解开囊来一看,内有缯缣百余匹。自此家事得以稍赡。自念所行非谊,因折弓弃矢,闭门读书,再不敢为非。遂出仕至此官位。从那时算至今岁,凡二十七年了。昨蒙君侯台旨,召侍王公之宴。初召时就有些心惊肉颤,不知其由。自料道决无他事,不敢推辞。及到席间灯下,一见王公之貌,正是我向时推在崖下的少年,相貌一毫不异。一拜之后,心中悚惕,魂魄俱无。晓得冤业见在面前了。自然死在目下,只消延颈待刃,还有甚别的说话来?幸得君侯知我甚深,不敢自讳。而今再无可逃,敢以身后为托,不使吾暴露尸骸足矣。”言毕大哭。太守也不觉惨然。欲要救解,又无门路。又想道:“既是有此冤业,恐怕到底难逃。”似信不信的,且看怎么?
太守叫人悄地打听,副大使起身了来报,再伺候有什么动静,快来回话。太守怀着一肚子鬼胎,正不知葫芦里卖出甚么药来。还替李参军希冀道:“或者酒醒起来,忘记了便好。”须臾之间,报说副大使睡醒了,即叫了左右进去。不知有何吩咐。太守叫再去探听。只见士真刚起身来,便问道:“昨夜李某,今在何处?”左右道:“蒙副大使发在郡狱。”士真便怒道:“这贼还在,快枭他首来!”左右不敢稽迟,来禀太守,早已有探事的人飞报过了。太守大惊失色,叹道:“虽是他冤业,却是我昨日不合举荐出来,害了他也!”好生不忍。没计奈何,只得任凭左右到狱中斩了李参军之首。正是:
阎王注定三更死,
并不留人到四更。
眼见得李参军做了一世名流,今日死于非命。左右取了李参军之头,来士真跟前献上取验。士真反复把他的头看了又看,哈哈大笑,喝叫:“拿了去!”士真梳洗已毕,太守进来参见,心里虽有此事恍惚,却装做不以为意的坦然模样,又请他到自家郡斋赴宴。逢迎之礼,一发小心了。士真大喜,比昨日之情,更加款洽。太守几番要问他,嗫嚅数次,不敢轻易开口。直到见他欢喜头上,太守先起,请罪道:“有句说话,斗胆要请教副大使。副大使恕某之罪,不嫌唐突,方敢启口。”士真道:“使君相待甚厚,我与使君相与甚欢,有话尽情直说,不必拘忌。”太守道:“某本不才,幸得备员,叨守一郡。副大使车驾枉临,下察弊政,宽不加罪,恩同天地了。昨日副大使酒间,命某召他客助饮。某属郡僻小,实无佳宾可以奉欢宴者。某愚不揣事,私道李某善能饮酒,故请命召之。不想李某愚戆,不习礼法,触忤了副大使,实系某之大罪。今副大使既已诛了李某,李某已伏其罪,不必说了。但某心愚鄙,窃有所未晓。敢此上问,不知李某罪起于何处?愿得副大使明白数他的过误,使某心下洞然。且用诫将来之人,晓得奉上的礼法,不致舛错,实为万幸。”士真笑道:“李某也无罪过,但吾一见了他,便忿然激动吾心,就有杀之之意。今既杀了,心方释然,连吾也不知所以然的缘故。使君但放心吃酒罢,再不必提起他了。”宴罢,士真欢然致谢而行,又到别郡去了。来这一番,单单只结果得一个李参军。
太守得他去了,如释重负,背上也轻松了好些。只可惜无端害了李参军,没处说得苦。太守记着狱中之言,密地访问王士真的年纪,恰恰正是二十七岁,方知太行山少年被杀之年,士真已生于王家了。真是冤家路窄,今日一命讨了一命。那心上事,只有李参军知道。连讨命的做了事,也不省得。不要说旁看的人,那里得知这些缘故!太守嗟叹怪异,坐卧不安了几日。因念他平日交契的分上,又是举他陪客,致害了他,只得自出家财,厚葬了李参军。常把此段因果劝人,教人不可行不义之事。有诗为证:
冤债原从隔世深,
相逢便起杀人心。
改头换面犹相报,
何况容颜俨在今!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