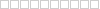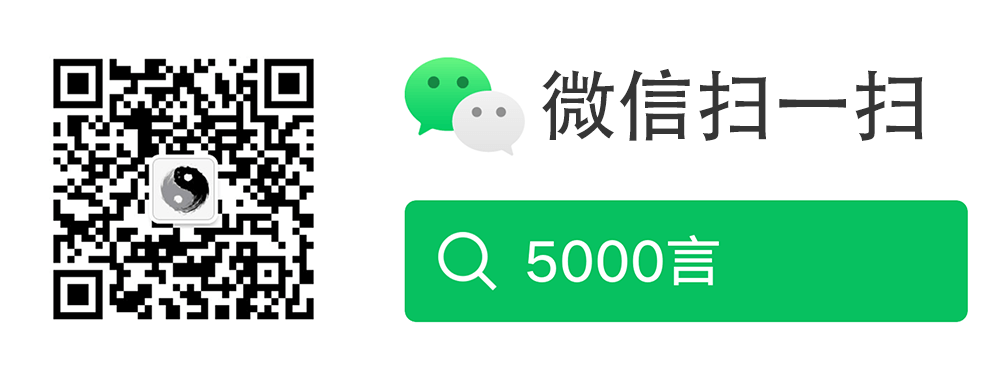寄生附
本文出自《聊斋志异》卷十二
【原文】
寄生,字王孙,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认父,谓有夙惠,钟爱之。长益秀美,八九岁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择偶。父桂庵有妹二娘,适郑秀才子侨,生女闺秀,慧艳绝伦。王孙见之,心切爱慕,积久,寝食俱废。父母大忧,苦研诘之,遂以实告。父遣冰于郑,郑性方谨,以中表为嫌,却之。王孙逾病。母计无所出,阴婉致二娘,但求闺秀一临存之。郑闻,益怒,出恶声焉。父母既绝望,听之而已。
郡有大姓张氏,五女皆美,幼者名五可,尤冠诸姊,择婿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孙,自舆中窥见,归以白母。母沈知其意,见媒媪于氏,微示之。媪遂诣王所。时王孙方病,讯知,笑曰:“此病老身能医之。”芸娘问故。媪述张氏意,极道五可之美。芸娘喜,使媪往候王孙。媪入,抚王孙而告之。王孙摇首曰:“医不对症,奈何!”媪笑曰:“但问医良否耳。其良也,召和而缓至,可矣。执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亦痴乎?”王孙欷歔曰:“但天下之医,无愈和者。”媪曰:“何见之不广也?”遂以五可之容颜发肤,神情态度,口写而手状之。王孙又摇首曰:“媪休矣!此余愿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复听矣。媪见其志不移,遂去。
一日,王孙沉痼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极,跃然而起。急出舍,则丽人已在庭中。细认之,却非闺秀,着松花色细褶绣裙,双钩微露,神仙不啻也。拜问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于情者,而独钟闺秀,使人不平。”王孙谢曰:“生平未见颜色,故目中止一闺秀。今知罪矣!”遂与要誓。方握手殷殷,适母来抚摩,蘧然而觉,则一梦也。回思声容笑貌,宛在目中,阴念:“五可果如所梦,何必求所难遘?”因而以梦告母。
母喜其念少夺,急欲媒之。王孙恐梦见不的,托邻妪素识张氏者,伪以他故诣之,嘱其潜相五可。妪至其家,五可方病,靠枕支颐,婀娜之态,倾绝一世。近问:“何恙?”女默然弄带,不作一语。母代答曰:“非病也。连日与爹娘负气耳!”妪问故,曰:“诸家问名,皆不愿,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为母者劝之急,遂作意不食数日矣。”妪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真是玉人成双也。渠若见五娘,恐又憔悴死矣!我归,即令倩冰,如何?”五可止之曰:“姥勿尔!恐其不谐,益增笑耳!”妪锐然以必成自任,五可方微笑。妪归,复命,一如媒媪言。王孙详问衣履,亦与梦合,大悦。意虽稍舒,然终不以人言为信。
过数日,渐瘳,秘招于媪来,谋以亲见五可。媪难之,姑应而去。久之,不至。方欲觅问,媪忽忻然来曰:“机幸可图。五娘向有小恙,日令婢辈将扶,移过对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缓涩,委曲可以尽睹矣。”王孙喜。明日,命驾早往,媪先在焉。即令絷马村树,引入临路舍,设座掩扉而去。少间,五可果扶婢出。王孙自门隙目注之。女从门外过,媪故指挥云树以迟纤步。王孙窥觇尽悉,意颤不能自持。未几,媪至,曰:“可以代闺秀否?”王孙申谢而返。始告父母,遣媒要盟。及妁往,则五可已别字矣。
王孙失意,悔闷欲死,即刻复病。父母忧甚,责其自误。王孙无词,惟日饮米汁一合,积数日,鸡骨支床,较前尤甚。媪忽至,惊曰:“何惫之甚?”王孙涕下,以情告。媪笑曰:“痴公子!前日人趁汝来,而故却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虽然,尚可为力。早与老身谋,即许京都皇子,能夺还也。”王孙大悦,求策。媪命函启遣伻,约次日候于张所。桂庵恐以唐突见拒,媪曰:“前与张公业有成言,延数日而遽悔之。且彼字他家,尚无函信。谚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桂庵从之。次日,二仆往,并无异词,厚犒而归。王孙病顿起,由此闺秀之想遂绝。
初,郑子侨却聘,闺秀颇不怿,既闻张氏婚成,心愈抑郁,遂病,日就支离。父母诘之,不肯言。婢窥其意,隐以告母。郑闻之,怒不医,以听其死。二娘怼曰:“吾侄亦殊不恶,何守头巾戒,杀吾娇女!”郑恚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贻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与女言,将使仍归王孙,若为媵。女俛首不言,意若甚愿。二娘商郑,郑更怒,一付二娘,置女度外,不复预闻。二娘爱女切,欲实其言。女乃喜,病渐瘥。
窃探王孙,亲迎有日矣。及期,以侄完婚,伪欲归宁。昧旦,使人求仆舆于兄。兄最友爱,又以居村邻近,遂以所备亲迎车马,先迎二娘。既至,则妆女入车,使两仆两媪护送之。到门,以毡贴地而入。时鼓乐已集,从仆叱令吹擂,一时人声沸聒。王孙奔视,则女子以红帕蒙首,骇极,欲奔,郑仆夹扶,便令交拜。王孙不知何由,即便拜讫。二媪扶女,径坐青庐,始知其闺秀也。举家皇乱,莫知所为。时渐濒暮,王孙不复敢行亲迎之礼。桂庵遣仆以情告张,张怒,遂欲断绝。五可不肯,曰:“彼虽先至,未受雁采,不如仍使亲迎。”父纳其言,以对来使。使归,桂庵终不敢从。相对筹思,喜怒俱无所施。张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舆马送五可至,因另设青帐于别室。而王孙周旋两间,蹀踱无以自处。母乃调停于中,使序行以齿,二女皆诺。及五可闻闺秀差长,称“姊”有难色,母甚虑之。比三朝公会,五可见闺秀风致宜人,不觉右之,自是始定。然父母恐其积久不相能,而二女却无间言,衣履易着,相爱如姊妹焉。
王孙始问五可却媒之故,笑曰:“无他,聊报君之却于媪耳。尚未见妾,意中止有闺秀;既见妾,亦略靳之,以觇君之视妾,较闺秀何如也。使君为伊病,而不为妾病,则亦不必强求容矣。”王孙笑曰:“报亦惨矣!然非于媪,何得一觐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见君,媪何能为?过舍门时,岂不知眈眈者在内耶?梦中业相要,何尚未知信耶?”王孙惊问:“何知?”曰:“妾病中梦至君家,以为妄,后闻君亦梦妾,乃知魂魄真到此也。”王孙异之,遂述所梦,时日悉符。父子之良缘,皆以梦成,亦奇情也。故并志之。
异史氏曰:父痴于情,子遂几为情死。所谓情种,其王孙之谓与?不有善梦之父,何生离魂之子哉!
【翻译】
王寄生,字王孙,是大名府的名士。父母因为他在襁褓里就能认出父亲,认为他天生聪慧,对他十分钟爱。长大以后,他越发秀美,八九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十四岁就进了府学。王寄生常常想自己选择配偶。他的父亲王桂庵有个妹妹二娘,嫁给秀才郑子侨,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闺秀,长得艳丽,生得聪明,是举世无双的女子。王寄生见到她以后,心中十分爱慕,时间一长,就到了寝食俱废的地步。父母万分忧虑,苦苦地追问他是怎么回事,王寄生就说出了实情。父亲请媒人到郑家提亲,但郑子侨生性固执严谨,认为表亲不可通婚,便拒绝了这门亲事。王寄生病得更重了。他母亲芸娘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暗中托人委婉地跟二娘商量,只求闺秀能到王家来一次,看一看王寄生。郑子侨听说后,更加愤怒,便说了些很不好听的话,王寄生父母已经绝望了,只好听之任之了。
郡里有个姓张的大户人家,生的五个女儿都很美丽,最小的叫五可,比她的姐姐们都还要美艳,正在挑选女婿还没有许人。一天,五可在上坟的路上遇到王寄生,从车子里窥见他的样子,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探明了五可的心思,就见了媒婆于氏,暗中示意她去说媒。于氏便来到王家。这时王寄生还病着,于氏一听他的病情,便笑着说:“这个病我老婆子能治好。”芸娘问是怎么回事。于氏便叙述了张家的意思,极口称赞五可的美貌。芸娘很高兴,让于氏去见王寄生。于氏进了屋子,抚摸着王寄生,并且告诉他自己来的意思。王寄生摇摇头说:“医不对症,又有什么用啊!”于氏笑着说:“看病只问医生的医术是否高明。如果医术高明,即使请的是医和,来的却是医缓,一样可以治病。如果固执地认准一个人要他治病,即使死守也要等他,这不是太傻了吗?”王寄生抽泣着说:“不过天下的医生,没有人能超过医和。”于氏说:“你的见识怎么这么不广啊?”接着,她就把五可的容颜、皮肤、神情态度,连说带比划地给王寄生描绘了一番。王寄生又摇摇头说:“妈妈不必再说了!这个人不是我心里想念的。”说完,转过身冲着墙壁,不再听于氏说了。于氏见王寄生的想法不可动摇,只好走了。
一天,王寄生病得昏沉沉的,忽然一个丫环走进来说:“你思念的人到了!”王寄生高兴极了,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起来,急忙跑出了屋子,发现一个美人已经站在庭院里。王寄生细细地辨认,却不是闺秀,只见她身穿松花色细褶绣裙,微微露出双脚,真是如同神仙下凡。王寄生上前施礼,请问姓名。姑娘回答说:“我是五可。你的一片深情都只在闺秀的身上,让人心中不平。”王寄生谢罪道:“我生平从未见过你的容貌,所以眼睛里只有一个闺秀,今天我才知罪了!”说完,就和五可定了誓约。王寄生正亲热地握着五可的手,恰好母亲来抚摩他,他惊喜地醒过来,这才发现刚才是一场梦。他回想五可的音容笑貌,好像还在眼前,不由心中暗想:“五可果真像梦中见到的一样,又何必去追求那难于求到的闺秀呢?”于是,他就把梦见五可的经过告诉了母亲。
芸娘很高兴儿子的念头已经有所改变,急忙想找人去张家说媒。王寄生唯恐梦中所见不真,便托一位平素和张家相识的邻居老妈妈,假装有什么事到张家去,嘱咐她暗中相看五可。老妈妈来到张家时,五可正在生病,头靠在枕头上,手托着香腮,一副婀娜动人的姿态,真是倾国倾城的美貌。老妈妈走近前问道:“是什么病呀?”五可默默地玩弄着衣带,一句话也不说。母亲代她回答说:“不是生病。是这几天在跟爹妈斗气呢!”老妈妈问是什么原因,母亲说:“好多人家来提亲,她都不愿意,一定要是王家的王寄生才肯嫁。因为我这个当妈的劝她急了,她就发了脾气,好几天不吃饭。”老妈妈笑着说:“姑娘如果配王郎,真是天生的一对玉人。他如果见了五娘,恐怕又要憔悴死了!我回去告诉王家,就让他家请媒人来提亲,怎么样?”五可制止她说:“妈妈别这么做!只怕人家不同意,更会招人笑话!”老妈妈毅然表示一定办成这事,五可这才微笑着答应了。老妈妈回到王家复命,讲得和媒婆说的一样。王寄生详细地询问五可的衣着,也和梦中见到的一样,大为高兴。王寄生的心情虽然稍稍舒缓了一些,但是始终不敢全信别人说的话。
过了几天,王寄生的病渐渐好了,他秘密地把媒婆于氏招来,和她商量要亲眼见一见五可。于氏觉得很为难,姑且答应下来就走了。过了好久,于氏也没有来。王寄生正要找人去问,于氏忽然高高兴兴地来了,说:“幸好有机可图了。五娘一直都有小病,每日就让丫环扶着,到对面院子散步。公子先去埋伏在一边等候,五娘行动缓慢,你就可以把她看个清清楚楚了。”王寄生很高兴。第二天,王寄生早早地让人备马前往,于氏已经先等在那里了。就让他把马系在村外的树上,然后领他进了临街的一间屋子,让他坐下,关上门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五可果然扶着丫环出来了。王寄生从门缝中注视着五可。五可从门外走过,于氏故意指点着云呀树的,来放缓五可的脚步。王寄生把五可看了个清清楚楚,不禁心跳加快,不能自持。不一会儿,于氏来了,问道:“可以代替闺秀吗?”王寄生向于氏道谢后就回家了。王寄生回家后,立刻把相看五可的事告诉父母,派媒人去张家订亲。等媒人前往张家一说,却发现五可已经许给别人了。
王寄生大失所望,后悔郁闷得要死,一下子又病倒了。父亲很是忧虑,怪他是自己误了好事。王寄生无言以对,每天只饮一碗米汤,过了几天,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躺在床上,比上一次病得还要厉害。这一天,于氏忽然来了,吃惊地问:“你怎么病成这样呢?”王寄生流下眼泪,把实情告诉她。于氏笑着说:“真是个痴公子!前些日子是人家来追你,你却故意拒绝人家;现在是你求人家,哪能说成就成呢?虽然如此,倒还可以想想办法。早点儿和我老婆子商量,即使嫁给了京城的皇子,也能够替你夺回来。”王寄生大为高兴,便请教有何计策。于氏便让他写好一封书信,派人送往张家,并约好第二天在张家等候。王桂庵担心会因为唐突行事而被张家拒绝,于氏说:“前些日子我和张公已经有约在先,延迟了几天,是他们忽然反悔的。况且说五娘已经许给别人,并没有什么书信帖子。俗语说:‘先做饭的人先吃。’有什么好怀疑的!”王桂庵听从了她的意见。第二天,两个仆人前往张家下聘,张家没说什么二话,厚厚地犒赏了他们。王寄生的病也一下子好了,从此他再也不去想闺秀了。
起初,郑子侨拒绝了王家的聘礼,闺秀很不高兴。等到听说王家和张家结成婚姻,心情更加抑郁,就病倒了,一天比一天憔悴。父母问她是怎么回事,她也不肯说。丫环窥探出闺秀的心思,悄悄地告诉她的父母。郑子侨听说后非常生气,不给闺秀请医生看病,听任她病死。二娘埋怨道:“我侄子也不差,何必死守那些陈腐的清规戒律,害死我们的女儿呢!”郑子侨恼羞成怒地说:“就你生的这种女儿,不如早点儿死掉,免得被人家当成笑柄!”从此以后,夫妻俩反目成仇。二娘跟女儿商量,还让她嫁给王寄生,但是只能做小老婆了。闺秀低下头不说话,看上去好像还很愿意。二娘又跟郑子侨商量,郑子侨更加愤怒,把这事全都交给二娘处理,将女儿置之度外,不再干涉这桩婚事。二娘爱女心切,就想把她的话变成现实,闺秀于是高兴起来,病也渐渐好了。
二娘暗中探听到王寄生迎亲的日期已经确定。到了那一天,二娘便以侄子要结婚,假装要回娘家探望。天刚亮,她就派人到哥哥家借车马。王桂庵对妹妹最为友爱,又因为两个村子靠得很近,就派准备用来迎亲的车马先去迎接二娘。车马一到,二娘就为女儿装扮好送上车,派两个仆人和两个仆妇护送。车马来到王家,便用红毡铺地,将闺秀接了进去。这时鼓乐已经准备好,仆人便喝令开始吹打起来,一时间人声鼎沸,鼓乐齐鸣。王寄生跑出来一看,只见女子用红帕蒙着头,不由十分惊骇,转身就要跑;郑家的两个仆人上前将王寄生夹扶在中间,就让他和新人拜堂。王寄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拜完了天地。两个仆妇扶着女子,径直进了洞房,这才知道她竟是闺秀。一时间,全家慌乱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渐渐地到了傍晚,王寄生也不再敢去张家迎接新人了。王桂庵派仆人把这个情况告诉张家,张家听了非常气愤,就想断绝这门亲事。五可不同意,说:“她虽然先到了,但是没有正式下聘礼,不如仍旧让王家来迎亲。”父亲采纳了她的意见,并且告诉了来送信的仆人。仆人回来报告了情况,但王桂庵终究不敢按张家的意思办。一家人坐在一起筹划商量,都被弄得高兴不是,发火也不是。张家等了很久,知道王家不会来迎亲了,便也派车马将五可送到王家。王家就在另外的房间也设了洞房,王寄生在两个洞房之间往来周旋,不知怎么办才好。于是,芸娘从中调解,让五可和闺秀二人根据岁数排列长次,两个姑娘都同意了。五可听说闺秀稍微大一点,就不是很愿意叫她姐姐,芸娘很是担忧。等到结婚第三天,两人在公婆面前见面,五可见闺秀很有风致,举止大方,不自觉地尊她为姐姐,从此,两位新娘才定了长次。王桂庵夫妇担心时间长了她们不能和睦共处,但两个媳妇却从来没有闹过矛盾,互相交换衣服,相亲相爱像姐妹一样。
这时,王寄生才问起五可为什么当初要拒绝婚事,五可笑着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报复你拒绝于媒婆提亲。还没有见到我的时候,你的心中只有一个闺秀;即使见了我以后,我也要庄重一点儿,来看你对待我的态度,和对待闺秀是不是一样。假使你为了她生病,却不为我生病,我也就不会强求你一定要娶我了。”王寄生笑着说:“报复得也够惨的!要不是于媒婆,我又怎么能一睹你的芳容呢?”五可说:“是我自己想见你,于媒婆她怎么能办得到呢?经过那家门前时,我难道不知道里面有个人直勾勾盯着我看吗?梦里都已经和你约定了,你为什么还不相信呢?”王寄生吃惊地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做的梦?”五可说:“我生病的时候做梦到了你家,以为很荒唐,后来听说你也做了个梦,我这才知道我的魂魄真的到过这里。”王寄生觉得很神奇,便讲述了自己做的那个梦,和五可做梦的时辰日期都符合。王桂庵父子的良缘都是通过梦而成的,这也可以称得上是神奇的爱情了。所以一并记载下来。
异史氏说:父亲痴迷于爱情,儿子也几乎为情而死。所谓的情种,说的就是王孙这样的人吧?如果没有一个善于做梦的父亲,又怎么会生出一个为爱离魂的儿子呢!
【点评】
本篇是上篇《王桂庵》的续篇。寄生即上篇王桂庵之子,王桂庵和芸娘在本篇也仍活动着。这在《聊斋志异》的结构中可谓绝无仅有。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大概与蒲松龄有意翻空出奇,打算在同一模式下展现不同的故事情节有关。“异史氏曰”说:“父痴于情,子遂几为情死。所谓情种,其王孙之谓与?不有善梦之父,何生离魂之子哉!”但明伦说:“此幅以‘情种’二字为根,‘离魂’二字为线。”可以作为比照理解《王桂庵》和《寄生》的钥匙。
由于本篇是从形式的变化上谋篇布局,故在人物性格和内容描写上有许多可争议之处。比如,王桂庵痴情于芸娘,可谓情种,但寄生见异思迁,是否也称得上是情种?在《王桂庵》篇,芸娘不能接受二女共嫁一夫的现实,这大概是明清时期正经人家少女,尤其是父母们的婚姻底线,但本篇中不仅五可和闺秀乐于接受共嫁的现实,大事化小,父母也竟然接受,尤其是闺秀的父亲郑秀才既然在“中表为嫌”上可以拒婚,在共嫁问题上更不可能不作梗发声,大发雷霆,这些,都是读者要探索而作品回避了的地方。不过,单纯从文学技巧上看,本篇的确充满浪漫气息,“反复展玩,有如山阴道上行,令人应接不暇,及求其运笔之妙,又如海上三神山,令人可望而不可即”(但明伦评)。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