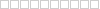语言艺术中的鼠文化:鼠诗、鼠文和鼠戏
上至古诗古文,下至戏曲儿歌,鼠一直是语言艺术中经常关注的对象。文人雅士们以鼠入题,或称赞其聪慧狡黠,或讥讽其偷盗祸害,抑或是以鼠喻人,使鼠成为了语言艺术中不老的题材。
鼠作为十二生肖之首,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其小小的躯体、线形的眼睛以及矫健的身手,鼠不仅受到了普通百姓的青睐,就连不少文人墨客也在语言的长廊中为鼠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鼠诗
早在《诗经》中就有了关于鼠的诗歌《硕鼠》。这首诗以人们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老鼠形象来比喻统治阶级,形象而深刻地揭示出奴隶主们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可见,老鼠作为贪婪、狡猾以及罪恶的象征古已有之。
当然,也有对鼠大家称赞的。晋代诗人郭璞有一首《飞鼠赞》:“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飞鸣鼓翰,倏然皆腾。用无常所,惟神斯凭。”尾能翔,髯能飞,其迅疾、矫健之姿被诗人刻画得淋漓尽致。清代的张劭还有一首《银鼠诗》:“杏山穴多耀灵鼯,猎网追风捕几何?窜地捷于逃月兔,跳空亮比掷星梭。松林溜粉宵还闭,雪窑争辉冷却过。总为微名倖世宝,新来冠服借伊多。”在诗人笔下,银鼠捷如月兔,亮如飞梭,令人目不暇接。
鼠文
《晏子春秋》中就有一篇“患社鼠”的文章:“景公问于晏子曰:‘治国何患?’晏子对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谓也?’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晏子以社鼠之名巧妙对答,将社鼠与朝廷中的奸臣佞子联系起来,也起到了很好的讽谏作用。
此外,在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柳宗元的《三戒》、苏东坡的《黠鼠赋》当中,都有对鼠的形象描绘,此不一一赘述。
鼠戏
在昆曲《十五贯》中,有个叫“娄阿鼠”的奸狡小人,因为贪图十五贯钱而杀了人,并在行凶后潜逃。苏州知府况钟为了缉拿凶犯,化装成“测字先生”,与娄阿鼠相遇。娄阿鼠作贼心虚,他请测字先生测吉凶,况钟巧妙地以鼠为喻,借助子与鼠的属相关系作文章,展开了一段妙趣横生的对话:
娄阿鼠:先生,小弟贱名娄阿鼠,这个老鼠的鼠字,你可测得出?
况钟:鼠乃十二生肖之首,岂不是个造祸之端么?依字理而断,一定是偷了人家的东西,造成这桩祸事来的。
娄阿鼠:你看我往后可有是非口舌连累得着?
况钟:怎说连累不着,目下就要败露了。
娄阿鼠:怎么说?
况钟:你问的鼠字,目下正交子月,乃当今之时,只怕这官司就要明白了。
娄阿鼠:先生,可能窜得出?
况钟:若是走,今日就要动身。到了明日,就走不掉了。
娄阿鼠:为什么?
况钟:鼠字头是个臼字,原是两个半日,合为一日之意。若到明日,就算两日,就走不掉了。
娄阿鼠:啊呀!现在天色已晚,叫我怎么走呢?
况钟:待我算算看,鼠属巽,巽属东,东南方去的好。
娄阿鼠:东南方?先生再费心看看,是水路太平,还是陆路无事?
况钟:待我算算看,鼠属子,子属水,水路去的好……
在这段戏文里,鼠与贼成了同义词。面对作贼心虚的娄阿鼠,况钟借助属相与人生的关系,使娄阿鼠在不知不觉中承认了自己是凶手。在这里,况钟做足了鼠字的文章,娄阿鼠的“鼠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还有以鼠为成语、以鼠为灯谜、以鼠为歇后语的,多如繁星,举不胜举。这也是生肖文化之所以保持永久魅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延伸阅读
来之邵“首鼠两端”
宋代庄绰所著的《鸡肋编》中记载了北宋元佑年间来之邵“首鼠两端”的事例:“元佑末”,已有“绍述”之论。时,来之邵为御史,议事率多首鼠,世目之为“两来子”。来之邵身为御史,议事时却常常动摇不定,首鼠两端,因而人们叫他“两来子”。“来”为来之邵的姓氏;“子”,即十二生肖中的鼠。以“子”为后缀,听起来仿佛是夫子之类的赞美之词,实则隐含着首鼠两端的批评,造成如此效果的因素,就是生肖中子与鼠的对应。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