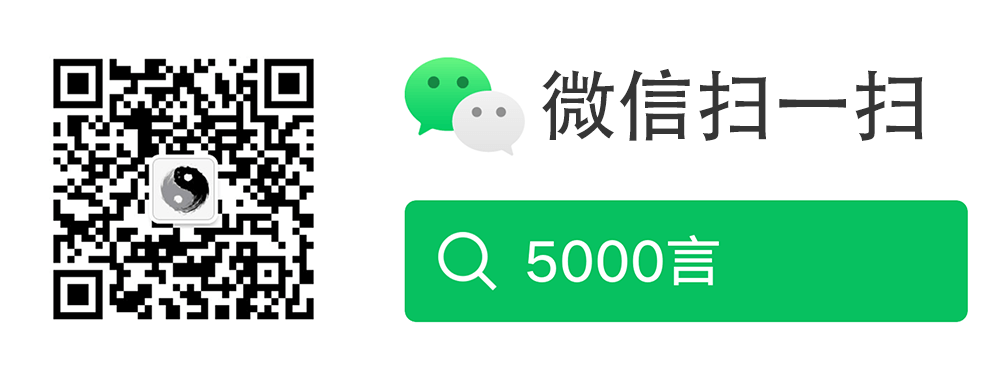问辩
查看翻译 【原文】
或问曰:“辩安生乎?”
或问曰:“辩安生乎?”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翻译】
有人问道:“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问的人又说:“君主不明智,因而产生辩说,这是为什么呢?”
回答说:“在英明君主统治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法律是处理政事的唯一准绳。除命令以外,国家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外,国家没有第二种处理政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为不符合法令的都必须禁止。如果他没有法令作依据却可以对付诈骗、应付事变、谋取利益、推断事理,君主必须采纳他的言论而责求其效果。言论与实效相一致,就给予大的赏赐;言论与实效不一致,就重重地处罚。如果这样,那么愚笨的人害怕获罪就不敢讲话,聪明的人也不敢争辩。这就是所以不产生辩说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君主下达了命令,而民众就用文化学术反对它;官府公布了法规,而民众就用个人行为违反它。君主反而放弃法令而尊重学者的聪明行为,这就是世上有这样多的人从事文学的原因。言行是要以功用为它的目标的。如果磨利了箭瞎射一气,箭头也未尝不可以射中微小的东西,然而这不能叫善射,因为它没有设定具体目标。如果设定五寸大小的箭靶,在十步之远拉弓射箭,不是善射的羿和逄蒙就不能肯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目标。因此,有固定目标,那么羿和逄蒙因为可以射中五寸大小的箭靶被称为巧射;没有固定目标,那么瞎射一气射中了微小的东西也是拙射。现在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作为目的,言论虽然分析入微,行为虽然非常坚定,也就像胡乱放箭一样。所以乱世听取言论,以不知所云为明察,以博学多文为雄辩;观察行为,以远离社会为贤能,以违抗君主为刚直。君主喜欢“雄辩”、“明察”的言论,尊重“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人,虽然确立了行为的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没有人来加以肯定。因此,儒生、侠客多了,耕田打仗的人少了;“坚白”、“无厚”的辩说之词彰显了,国家的制度、法令就消亡了。所以说:“君主不明智,辩说也就产生了。”
【翻译】
有人问道:“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问的人又说:“君主不明智,因而产生辩说,这是为什么呢?”
回答说:“在英明君主统治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法律是处理政事的唯一准绳。除命令以外,国家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外,国家没有第二种处理政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为不符合法令的都必须禁止。如果他没有法令作依据却可以对付诈骗、应付事变、谋取利益、推断事理,君主必须采纳他的言论而责求其效果。言论与实效相一致,就给予大的赏赐;言论与实效不一致,就重重地处罚。如果这样,那么愚笨的人害怕获罪就不敢讲话,聪明的人也不敢争辩。这就是所以不产生辩说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君主下达了命令,而民众就用文化学术反对它;官府公布了法规,而民众就用个人行为违反它。君主反而放弃法令而尊重学者的聪明行为,这就是世上有这样多的人从事文学的原因。言行是要以功用为它的目标的。如果磨利了箭瞎射一气,箭头也未尝不可以射中微小的东西,然而这不能叫善射,因为它没有设定具体目标。如果设定五寸大小的箭靶,在十步之远拉弓射箭,不是善射的羿和逄蒙就不能肯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目标。因此,有固定目标,那么羿和逄蒙因为可以射中五寸大小的箭靶被称为巧射;没有固定目标,那么瞎射一气射中了微小的东西也是拙射。现在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作为目的,言论虽然分析入微,行为虽然非常坚定,也就像胡乱放箭一样。所以乱世听取言论,以不知所云为明察,以博学多文为雄辩;观察行为,以远离社会为贤能,以违抗君主为刚直。君主喜欢“雄辩”、“明察”的言论,尊重“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人,虽然确立了行为的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没有人来加以肯定。因此,儒生、侠客多了,耕田打仗的人少了;“坚白”、“无厚”的辩说之词彰显了,国家的制度、法令就消亡了。所以说:“君主不明智,辩说也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