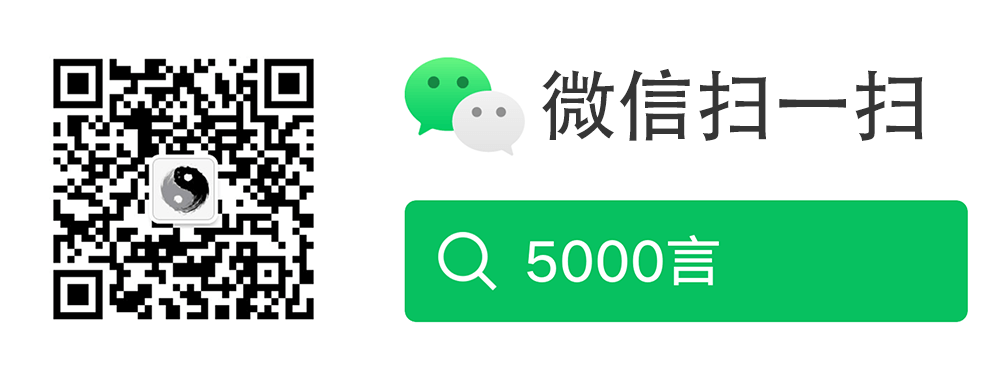难势
查看翻译 【原文】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则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则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醲(nóng)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醲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
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风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
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翻译】
慎到说:飞龙、腾蛇在云雾中飞行,云消雾散,它们就同蚯蚓、蚂蚁一样了,这是因为它们失去了飞行的凭借。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肖的人,是因为贤人权利小地位低;不肖的人能被贤人制服,是由于贤人权力大地位高。假如尧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连三个人也治理不了;而桀做了天子,能搞乱天下:我由此知道权势和地位是足以依靠的,而贤能和智慧是不值得羡慕的。一张不强劲的弩能把箭射得很高,那是风力推动的缘故;自己的品德不好,而命令却能推行,那是得力于众人帮助的缘故。如果尧以普通人身份在奴隶中施教,民众就不会听他的;而当他南面称王时,就能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由此看来,贤能和才智不足以让众人服从,而权势地位却足以使贤人屈服。
有人反驳慎到说:飞龙、腾蛇在云雾中飞行,我不认为龙蛇的飞行是不依托云雾这种势的。虽然如此,如果放弃贤能而专门依靠势,难道能足以治理国家吗?这是我没有见到的。有那种云雾之势而能依托它飞行的,这是龙蛇的资质好的缘故;现在云气浩盛而蚯蚓不能乘云,雾气浓烈而蚂蚁不能游雾,这种有盛云浓雾却不能依托它们飞行,是蚯蚓、蚂蚁的资质薄劣的缘故。现在夏桀、商纣南面称王统治天下,把天子的权威当作云雾,而天下还是免不了大乱,这是因为夏桀、商纣的资质薄劣的缘故。
况且这个人以为用尧的势可以治理天下,尧的势与桀的势有什么差别呢,这是扰乱天下的说法。所谓势,并不是一定能够让贤能的人利用,而不肖的人不能利用。贤能的人利用势天下就能治,不肖的人利用势天下就会乱。从人的本性来说,贤能的人少而不肖的人多,而用威势的好处来帮助扰乱天下的不肖之人,那么这是用势来扰乱天下的多,而用势来治理天下的少了。势这个东西,是便于统治却有利于祸乱的。所以《周书》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它将飞入城市,逢人便吃。”如果让不肖的人凭借权势,就是给老虎添上翅膀。夏桀、商纣筑高台掘深池耗尽了民力,用炮烙的酷刑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纣能够这样放肆地干坏事,是因为有天子的威势作为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不等他们干一件坏事就被处死了。势是滋生虎狼之心、成就暴乱之事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天下的大祸害。势对于治和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而那种专讲势可以治天下的人,他的智力所达到的程度是多么浅薄啊。
如果有良好的马匹和坚固的车辆,让奴仆来驾驶就会被人笑话,让王良驾驶就会日行千里。车马没有不同,有的人驾驶可以到达千里,有的人驾驶遭人嘲笑,灵巧和笨拙相差太远了。现在把国君的位置当作车,把权势当作马,把发号施令当作马缰绳,把刑罚当作马鞭子,让尧、舜来驾驶就会天下大治,让桀、纣驾驶就会天下大乱,那么贤君和暴君相差就太远了。想赶上快速奔驰的车马到达远方,不晓得任用王良;想增进利益免除祸害,不晓得任用贤能的人:这是不知道类比带来的危害。那个尧、舜也是治理百姓的王良啊。
又有人反驳这个反驳的人说:慎到认为完全可以依靠势来处理官职范围内的事;而您说“一定要等待贤人出现才能治理好天下”,这是不对的。势的名称虽然只有一个,但它有无数不同的含义。势如果一定出于自然,那就不必讨论势了。我所要说的势,是人为设立的。尧、舜降生于世而处在君主的位置,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天下,那是由于势治的缘故;桀、纣也降生于世而处在君主的位置,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那是由于势乱的缘故。所以说:“势治了的就不可能再乱,势乱了的就不可能再治。”这是自然之势,不是人为设立的势。像我说的势,只是说人所设立的势罢了,贤人能做什么事呢?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卖矛和盾的人,称赞他的盾十分坚固,‘什么东西都刺不穿它’,过了一会儿又称赞它的矛说:‘我的矛十分锋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有人责难他说:‘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不能回答了。”因为不能被刺穿的盾和什么都能刺穿的矛,按照判断是不能同时成立的。按照贤治的原则,贤人是不受约束的;而按照势治的原则,无论什么人都要受约束,“不要约束”的贤治和“什么都要约束”的势治,就构成了矛盾的说法。这样贤治与势治不能相容也就明明白白了。
况且像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年出现一个,就算是一个接一个降生了。而世上治理国家的君主不断出现的是中才,我所要讲的势,就是针对这些中才。中才的君主,与上比较不及尧、舜,与下比较也不会做桀、纣。这样的君主守住法度、据有势位就能治理国家,背弃法度、抛弃势位就会扰乱国家。现在废弃势位、背离法度而等待尧、舜,尧、舜来了国家才能治理,这是千世乱而一时治。如果守住法度、握有势位而等待桀、纣,桀、纣来了国家才出现混乱,这是千世治而一时乱。况且治千世而乱一时,与治一时而乱千世,就好比骑着好马分道而驰,二者相距会越来越远。如果放弃了矫正曲木的工具,丢掉了测量长短的尺度,让奚仲来造车,连一个轮子也做不成。没有庆功赏赐的鼓励,放弃势位和法度,即使尧、舜挨家挨户劝说,逢人就宣传辨析,连三家也治理不好。势足以利用来治理国家是明明白白的,却说“一定要等待贤人来治理国家”,这也是不对的。
况且要一百天不吃饭的人等待吃一餐美食,这个饥饿的人是活不了的;现在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君来治理当今世上的民众,这好比要人们等待美食来解救饥饿的说法。反驳慎到的人说“好的马匹和坚固的车,奴仆驾驶就会被人笑话,王良驾驶就可以日行千里”,我认为不是这样。等待越地会在海中游泳的人来救中原落水的人,越地的人虽然会游泳,而中原落水的人已经不行了。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今天的马匹,也像等待越地的人来救中原落水的人一样,行不通也是明明白白的。好的马和坚固的车,五十里有一个驿站,让一个中等水平的人来驾驶,用较快的速度驰向远方,是可以达到的,就是一千里也能在一定时间到达,何必要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不是让王良来驾,就一定让奴仆来败坏它;治国,不是让尧、舜来治,就一定让桀、纣来扰乱它。这种味道不是糖蜜一样甘甜,就一定是苦莱、亭历一样苦涩。这都是在制造说辞,背离常理,趋于极端的议论,怎么可以用来责难那些有道理的言论呢?您的贤治的议论赶不上势治的理论啊。
【翻译】
慎到说:飞龙、腾蛇在云雾中飞行,云消雾散,它们就同蚯蚓、蚂蚁一样了,这是因为它们失去了飞行的凭借。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肖的人,是因为贤人权利小地位低;不肖的人能被贤人制服,是由于贤人权力大地位高。假如尧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连三个人也治理不了;而桀做了天子,能搞乱天下:我由此知道权势和地位是足以依靠的,而贤能和智慧是不值得羡慕的。一张不强劲的弩能把箭射得很高,那是风力推动的缘故;自己的品德不好,而命令却能推行,那是得力于众人帮助的缘故。如果尧以普通人身份在奴隶中施教,民众就不会听他的;而当他南面称王时,就能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由此看来,贤能和才智不足以让众人服从,而权势地位却足以使贤人屈服。
有人反驳慎到说:飞龙、腾蛇在云雾中飞行,我不认为龙蛇的飞行是不依托云雾这种势的。虽然如此,如果放弃贤能而专门依靠势,难道能足以治理国家吗?这是我没有见到的。有那种云雾之势而能依托它飞行的,这是龙蛇的资质好的缘故;现在云气浩盛而蚯蚓不能乘云,雾气浓烈而蚂蚁不能游雾,这种有盛云浓雾却不能依托它们飞行,是蚯蚓、蚂蚁的资质薄劣的缘故。现在夏桀、商纣南面称王统治天下,把天子的权威当作云雾,而天下还是免不了大乱,这是因为夏桀、商纣的资质薄劣的缘故。
况且这个人以为用尧的势可以治理天下,尧的势与桀的势有什么差别呢,这是扰乱天下的说法。所谓势,并不是一定能够让贤能的人利用,而不肖的人不能利用。贤能的人利用势天下就能治,不肖的人利用势天下就会乱。从人的本性来说,贤能的人少而不肖的人多,而用威势的好处来帮助扰乱天下的不肖之人,那么这是用势来扰乱天下的多,而用势来治理天下的少了。势这个东西,是便于统治却有利于祸乱的。所以《周书》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它将飞入城市,逢人便吃。”如果让不肖的人凭借权势,就是给老虎添上翅膀。夏桀、商纣筑高台掘深池耗尽了民力,用炮烙的酷刑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纣能够这样放肆地干坏事,是因为有天子的威势作为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不等他们干一件坏事就被处死了。势是滋生虎狼之心、成就暴乱之事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天下的大祸害。势对于治和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而那种专讲势可以治天下的人,他的智力所达到的程度是多么浅薄啊。
如果有良好的马匹和坚固的车辆,让奴仆来驾驶就会被人笑话,让王良驾驶就会日行千里。车马没有不同,有的人驾驶可以到达千里,有的人驾驶遭人嘲笑,灵巧和笨拙相差太远了。现在把国君的位置当作车,把权势当作马,把发号施令当作马缰绳,把刑罚当作马鞭子,让尧、舜来驾驶就会天下大治,让桀、纣驾驶就会天下大乱,那么贤君和暴君相差就太远了。想赶上快速奔驰的车马到达远方,不晓得任用王良;想增进利益免除祸害,不晓得任用贤能的人:这是不知道类比带来的危害。那个尧、舜也是治理百姓的王良啊。
又有人反驳这个反驳的人说:慎到认为完全可以依靠势来处理官职范围内的事;而您说“一定要等待贤人出现才能治理好天下”,这是不对的。势的名称虽然只有一个,但它有无数不同的含义。势如果一定出于自然,那就不必讨论势了。我所要说的势,是人为设立的。尧、舜降生于世而处在君主的位置,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天下,那是由于势治的缘故;桀、纣也降生于世而处在君主的位置,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那是由于势乱的缘故。所以说:“势治了的就不可能再乱,势乱了的就不可能再治。”这是自然之势,不是人为设立的势。像我说的势,只是说人所设立的势罢了,贤人能做什么事呢?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卖矛和盾的人,称赞他的盾十分坚固,‘什么东西都刺不穿它’,过了一会儿又称赞它的矛说:‘我的矛十分锋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有人责难他说:‘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不能回答了。”因为不能被刺穿的盾和什么都能刺穿的矛,按照判断是不能同时成立的。按照贤治的原则,贤人是不受约束的;而按照势治的原则,无论什么人都要受约束,“不要约束”的贤治和“什么都要约束”的势治,就构成了矛盾的说法。这样贤治与势治不能相容也就明明白白了。
况且像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年出现一个,就算是一个接一个降生了。而世上治理国家的君主不断出现的是中才,我所要讲的势,就是针对这些中才。中才的君主,与上比较不及尧、舜,与下比较也不会做桀、纣。这样的君主守住法度、据有势位就能治理国家,背弃法度、抛弃势位就会扰乱国家。现在废弃势位、背离法度而等待尧、舜,尧、舜来了国家才能治理,这是千世乱而一时治。如果守住法度、握有势位而等待桀、纣,桀、纣来了国家才出现混乱,这是千世治而一时乱。况且治千世而乱一时,与治一时而乱千世,就好比骑着好马分道而驰,二者相距会越来越远。如果放弃了矫正曲木的工具,丢掉了测量长短的尺度,让奚仲来造车,连一个轮子也做不成。没有庆功赏赐的鼓励,放弃势位和法度,即使尧、舜挨家挨户劝说,逢人就宣传辨析,连三家也治理不好。势足以利用来治理国家是明明白白的,却说“一定要等待贤人来治理国家”,这也是不对的。
况且要一百天不吃饭的人等待吃一餐美食,这个饥饿的人是活不了的;现在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君来治理当今世上的民众,这好比要人们等待美食来解救饥饿的说法。反驳慎到的人说“好的马匹和坚固的车,奴仆驾驶就会被人笑话,王良驾驶就可以日行千里”,我认为不是这样。等待越地会在海中游泳的人来救中原落水的人,越地的人虽然会游泳,而中原落水的人已经不行了。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今天的马匹,也像等待越地的人来救中原落水的人一样,行不通也是明明白白的。好的马和坚固的车,五十里有一个驿站,让一个中等水平的人来驾驶,用较快的速度驰向远方,是可以达到的,就是一千里也能在一定时间到达,何必要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不是让王良来驾,就一定让奴仆来败坏它;治国,不是让尧、舜来治,就一定让桀、纣来扰乱它。这种味道不是糖蜜一样甘甜,就一定是苦莱、亭历一样苦涩。这都是在制造说辞,背离常理,趋于极端的议论,怎么可以用来责难那些有道理的言论呢?您的贤治的议论赶不上势治的理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