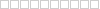第三十七回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
第三十七回·徐懋功初交秦叔宝
词曰:
人主荒淫成性,苍天巧弄盈危。群英一点雄心逞,戈满起尘埃。 攘攘不分身梦,营营好乱情怀。相看意气如兰蕙,聚散总安排。
——右调《乌夜啼》
天下最荼毒百姓的,是土木之工,兵革之事。剥了他的财,却又疲他的力。以至骨肉异乡,孤人之儿,寡人之妇,说来伤心,闻之酸鼻。却说炀帝,因沙夫人堕了胎,故将爱子赵王与他为嗣,命王义镌玉印赐他。又着朱贵儿迁在宝林院去,一同抚养赵王,自以为磐石之固。岂知天下盗贼蜂起,卒至国破家亡。
且说宇文弼、宇文恺得了旨意,遂行文天下,起人夫,吊钱粮,不管民疲力敝,只一味严刑重法的催督。弄得这些百姓,不但穷的驱逼为盗;就是有身家的,被这些贪官污吏,不是借题炙诈,定是赋税重征,也觉身家难保。要想寻一个避秦的桃源,却又无地可觅。其时翟让聚义瓦岗,朱灿在城父,高开道据北平,魏刁儿在燕,王须拔在上谷,李子通在东海,薛举在陇西,梁师都在朔方,刘武周在汾阳,李轨据河西,左孝友在齐郡,卢明月在涿郡,郝孝德在平原,徐元朗在鲁郡,杜伏威在章丘,萧铣据江陵。这干也有原系隋朝官员,也有百姓卒伍,各人啸聚一方劫掠。还有许多山林好汉,退隐贤豪,在那里看守天时,尚未出头。
再说窦建德,携女儿到单员外庄上安顿了。打账也要往各处走走。常言道:惺惺惜惺惺。话不投机的,相聚一刻也难过;若遇知己,就叙几年也不觉长远。雄信交结甚广,时常有人来招引他。因打听得秦叔宝避居山野,在家养母,雄信深为赞叹。因此也不肯轻身出头,甘守家园,日与建德谈心讲武。
光阴荏苒,建德在二贤庄,倏忽二载有余。一日雄信有事往东庄去了,建德无聊,走出门外闲玩。只见场上柳阴之下,坐着五六个做工的农夫,在那里吃饭。对面一条湾溪,溪上一条小小的板桥,桥南就是一个大草棚。建德慢慢的踱过桥来,站在棚下,看牛过水。但见一派清流,随轮带起;泉声鸟和,即景幽然。此时身心,几忘名利。正闲玩之间,远远望见一个长大汉子,草帽短衣,肩上背了行囊,坦胸露臂,忙忙的走来。场上有只猎犬,认是歹人,咆哮的迎将上去。那大汉见这犬势来得凶猛,把身子一侧,接过犬的后腿,丢入溪中去了。做工的看见,一个个跳起来喊道:“那里来的野鸟,把人家的犬丢在河里?”那汉道:“你不眼瞎,该放犬出来咬人的?”那做工的大怒,忙走近前,一巴掌打去。那汉眼快,接过来一折,那做工的扑地一交,扒不起来。惹得四五个做工的,齐起身来动手,被那汉打得一个落花流水。
建德站在对河看,晓得雄信庄上的人俱是动得手的,不去喝住他。以后见那汉打得利害,忙走过桥来喝道:“你是那里来的,敢走到这里来撒野?”那汉把建德仔细一认,说道:“原来是窦大哥,果然在这里!”扑地拜将下去。建德道:“我只道是谁,原来是孙兄弟,为甚到此?”那汉道:“小弟要会兄得紧,晓得兄携了令爱迁往汾州,弟前日特到介休各处寻访,竟无踪迹。幸喜途中遇着一位齐朋友,说兄在二贤庄单员外处,叫弟到此寻问,便知下落。故弟特特来访,不想恰好遇着。”原来这人姓孙名安祖,与窦建德同乡。当年安祖因盗民家之羊,为县令捕获笞辱。安祖持刀刺杀县令,人莫敢当其锋,号为摸羊公。遂藏匿在窦建德家,一年有余。恰值朝廷钦点绣女,建德为了女儿与他分散,直至如今。时建德便对安祖道:“这里就是二贤庄。”把手指道:“那来的便是单二员外了。”
雄信骑着高头骏马,跟着四五个伴当回来,见建德在门外,快跳下马来问道:“此位何人?”建德答道:“这是同乡敝友孙安祖。”雄信见说,便与建德邀入草堂。安祖对雄信纳头拜下去道:“孙安祖粗野亡命之徒,久慕员外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实慰平生。”雄信道:“承兄光顾,足见盛情。”雄信便分付手下摆饭。建德问安祖道:“刚才老弟说有一位齐朋友,晓得我在这里,是那个齐朋友?”安祖道:“弟去岁在河南,偶于肆中饮酒,遇见一个姓齐的,号叫国远,做人也豪爽有趣。说起江湖上这些英雄,他极称单员外疏财仗义,故此晓得,弟方始寻来。”雄信道:“齐国远如今在何处着脚?”安祖道:“他如今往秦中去寻什么李玄邃。说起来,他相知甚多,想必也要做些事业起来。”雄信叹道:“世路如此,这几个朋友料不能忍耐,都想出头了。”
须臾酒席停当,三人入席坐定。建德道:“老弟两年在何处浪游?近日外边如何光景?”安祖道:“兄住在这里,不知其细:外边不成个世界了。弟与兄别后,自燕至楚,自楚至齐,四方百姓,被朝廷弄得妻不见夫,父不见子,人离财散,怨恨入骨,巴不能个为盗,苟延性命。目今各处都有人占据,也有散而复聚的,也有聚而复散的,总是见利忘义,酒色之徒。若得似二位兄长这样智勇兼全的出来,倡义领众,四方之人,自然闻风响应。”建德见说,把眼只顾看单雄信,总不则声。雄信道:“宇宙甚广,豪杰尽多,我们两个算得什么?但天生此七尺之躯,自然要轰轰烈烈,做他一场,成与不成,命也。所争者,乃各人出处迟速之间。”孙安祖道:“若二位兄长皆救民于水火,出去谋为一番,弟现有千余人,屯扎在高鸡泊,专望驾临动手。”建德道:“准千人亦有限,只是做得来便好。倘然弄得王不成王,寇不成寇,反不如不出去的高了。”雄信道:“好山好水,原非你我意中结局。事之成败,难以逆料。窦兄如欲行动,趁弟在家,未曾出门。”
正说时,只见一个家人,转送朝报进来。雄信接来看了,拍案道:“真个昏君!这时候还要差官修葺万里长城,又要出师去征高丽,岂不是劳民动众,自取灭亡?就是来总管能干,大厦将倾,岂一木所能支哉!前日徐懋功来,我烦他捎书与秦大哥。今若来总管出征,怎肯放得他过?恐叔宝亦难乐守林泉了。”安祖道:“古人说得好,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今若不趁早出去收拾人心,倘各投行伍散去,就费力了。”建德道:“非是小弟深谋远虑,一则承单二哥高情厚爱,不忍轻抛此地;二则小女在单二哥处打扰,颇有内顾萦心。”雄信道:“窦大哥,你这话说差了。大凡父子兄弟,为了名利,免不得分离几时;何况朋友的聚散?至于令爱,与小女甚是相得,如同胞姊妹一般。况兄之女,即如弟之女也。兄可放心前去,倘出去成得个局面,来接取令爱未迟。若弟有甚变动,自然送令爱归还兄处,方始放心。”建德见说,不觉洒泪道:“若然,我父与女真生死而骨肉者也。”主意已定,遂去收拾行装,与女儿叮咛了几句,同安祖痛饮了一夜。到了明日,雄信取出两封盘缠:一封五十两,送与建德;一封二十两,赠与安祖。各自收了,谢别出门。正是:
丈夫肝胆悬如日,邂逅相逢自相悉。
笑是当年轻薄徒,白首交情不堪结。
如今再说秦叔宝,自遭麻叔谋罢斥回来,迁居齐州城外,终日栽花种竹,落得清闲。倏忽年余。一日在篱门外大榆树下闲看野景,只见一个少年,生得容貌魁伟,意气轩昂,牵着一匹马,戴着一顶遮阳笠,向叔宝问道:“此处有座秦家庄么?”叔宝道:“兄长何人?因何事要到秦家庄去?”这少年道:“在下是为潞州单二哥捎书与齐州秦叔宝的。因在城中搜寻,都道移居在此,故来此处相访。”叔宝道:“兄若访秦叔宝,只小弟便是。”叫家童牵了马,同到庄里。
这少年去了遮阳笠,整顿衣衫,叔宝也进里边,着了道袍,出来相见。少年送上书,叔宝接来拆览,乃是单雄信因久不与叔宝一面,晓得他睢阳斥职回来,故此作书问候。书后说此人姓徐名世勣,字懋功,是离狐人氏,近与雄信为八拜之交。因他到淮上访亲,托他寄此书。叔宝看了书道:“兄既是单二哥的契交,就与小弟一体的了。”分付摆香烛,两人也拜了,结为兄弟,誓同生死。留在庄上,置酒款待。豪杰遇豪杰,自然话得投机,顷刻间肝胆相向。叔宝心中甚喜,重新翻席,在一个小轩里头去,临流细酌,笑谈时务。
话到酒酣,叔宝私虑徐懋功少年,交游不多,识见不广,因问道:“懋功兄,你自单雄信二哥外,也曾更见甚豪杰来?”懋功道:“小弟年纪虽小,但旷观事势,熟察人情。主上摧刃父兄,大纲不正,即使修德行仁,还是个逆取顺守。如今好大喜功,既建东京宫阙,又开河道,土木之工,自长安直至余杭,那一处不骚扰遍了?只看这些穷民,数千百里来做工,动经年月,回去故园已荒,就要去,资费已竭,那得不聚集山谷,化为盗贼?况主上荒淫日甚:今日自东京幸江都,明日自江都幸东京;还要修筑长城,巡行河北,车驾不停,转输供应,天下何堪?那干奸臣,还要朝夕哄弄,每事逢君之恶。不出四五年,天下定然大乱!故此小弟也有意结纳英豪,寻访真主。只是目中所见,如单二哥、王伯当,都是将帅之才;若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恐还未能。其余不少井底之蛙,未免不识真主,妄思割据。虽然乘乱也能有为,首领还愁不保。但恨真主目中还未见闻。”叔宝道:“兄曾见李玄邃么?”懋功道:“也见来。他门第既高,识器亦伟,又能礼贤下士,自是当今豪杰。总依小弟识见起来,草创之君,不难虚心下贤。要明于用贤,不贵自己有谋,贵于用人之谋。今玄邃自己有才,还恐他自矜其才,好士下贤,还恐他误任不贤。若说真主,虑其未称。兄有所见么?”叔宝道:“如兄所云,将帅之才,弟所友东阿程知节,勇敢劲敌之人。又见三原李药师,药师曾云:王气在太原,还当在太原图之。若我与兄何如?”懋功笑道:“亦一时之杰。但战胜攻取,我不如兄;决机虑变,兄不如我。然俱堪为兴朝佐命,永保功名。大要在择真主而归之,无为祸首可也。”叔宝道:“天下人才甚多,据兄所见,止于此乎?”懋功道:“天下人才固多,你我耳目有限,再当求之耳。若说将帅之才,就兄附近孩稚之中,却有一人,兄曾识之否?”叔宝道:“这到不识。”懋功道:“小弟来访兄时,在前村经过,见两牛相斗,横截道中。小弟勒马道旁待他,却见一个小厮,年纪不过十余岁,追上前来道:‘畜生莫斗,家去罢。’这牛两角相触不肯休息,他大喝一声道:‘开!’一手揿住一只牛角,两下的为他分开尺余之地,将及半个时辰;这牛不能相斗,各自退去。这小厮跳上牛背,吹着横笛便走。小弟正要问他姓名,恰有一个小厮道:‘罗家哥哥,怎把我家牛角揿坏了?’小弟以此知他姓罗,在此处牧放,居止料应不远。他有这样膂力,若有人提携他,教他习学武艺,怕不似孟贲一流?兄可去物色他则个。”
何地无奇才,苦是不相识。
赳赳称干城,却从兔置得。
两人意气相合,扺掌而谈者三日。懋功因决意要到瓦岗,看翟让动静,叔宝只得厚赠资费,写书回复了单雄信。另写一札,托雄信寄与魏玄成。杯酒话别,两个相期,不拘何人择有真主,彼此相荐,共立功名。叔宝执手依依,相送一程而别,独自回来。
行不多路,只听得林子里发一声喊,跑出一队小厮来,也有十七八岁的,也有十五六岁的,十二三岁的,约有三四十个。后面又赶出一个小厮,年纪只有十余岁,下身穿一条破布裤,赤着上身,捏着两个拳头,圆睁一双怪眼,来打这干小厮。这干小厮见他来,一齐把石块打去,可是奇怪,只见他浑身虬筋挺露,石块打着,都倒激了转来。叔宝暗暗点头道:“这便是徐懋功所说的了。”
两边正赶打时,一个小厮被赶得慌,一交绊倒在叔宝面前。叔宝轻轻扶起道:“小哥,这是谁家小厮,这等样张致?”这小厮哭着道:“这是张太公家看牛的。他每日来看牛,定要妆甚官儿,要咱们去跟他。他自去草上睡觉。又要咱们替他放牛,若不依他,就要打。去跟他,不当他的意儿,又要打。咱们打又打他不过,又不下气伏事他,故此纠下许多大小牧童,与他打。却也是平日打怕了,便是大他六七岁,也近不得他,像他这等奢遮罢了。”叔宝想:“懋功说是罗家,这又是张家小厮,便不是,也不是个庸人了。”挪步上前,把这小厮手来拉住道:“小哥且莫发恼。”这小厮睁着眼道:“干你鸟事来!你是那家老子哥子,想要来替咱厮打么?”叔宝道:“不是与你厮打,要与你讲句话儿。”小厮道:“要讲话,待咱打了这干小黄黄儿来。”待洒手去,却又洒不脱。
正扯拽时,只见众小儿拍手道:“来了,来了!”却走出一个老子来,向前把这小厮总角揪住。叔宝看时,是前村张社长,口里喃喃的骂道:“叫你看牛不看牛,只与人厮打。好端端坐在家里,又惹这干小厮到家中嚷乱。你打死了人,叫我怎生支解?”叔宝劝道:“太公息怒,这是令孙么?”太公道:“咱家有这孙子来!是我一个老邻舍罗大德,他死了妻子,剩下这小厮,自己又被佥去开河,央及我管顾他。在咱家吃这碗饭,就与咱家看牛。不料他老子死在河上,却留这劣种害人。”叔宝道:“这等不妨,太公将来把与小子,他少宅上雇工钱,小子一一代还。”太公道:“他也不少咱工钱。秦大哥,你要领,任凭领去。只是讲过,惹出事来,不要干连着我。”叔宝道:“这断不干连太公,但不知小哥心下可肯?”那小厮向着太公道:“咱老子原把我交与你老人家的,怎又叫咱随着别人来?”太公发恼道:“咱招不得你,咱没这大肚子袋气。”一径的去了。
叔宝道:“小哥莫要不快。我叫秦叔宝,家中别无兄弟,止有老母妻房,意欲与你八拜为交,结做异姓兄弟,你便同我家去罢。”这小子方才喜欢道:“你就是秦叔宝哥哥么?我叫罗士信。我平日也闻得村中有人说哥哥弃官来的。说你有偌大气力,使得条好枪,又使得好锏。哥可怜见兄弟父母双亡,只身独自看顾,指引我小兄弟。莫说做兄弟,随便使令教诲,咱也甘心。”便向地下拜倒来。叔宝一把扶住道:“莫拜莫拜,且到家中,先见了我母亲,然后我与你拜。”果然士信随了叔宝回家。叔宝先对母亲说了,又叫张氏寻了一件短褂子,与他穿了,与秦母相见。罗士信见了道:“我少时没了母亲,见这姥姥,真与我母亲一般。”插烛也似拜了八拜,开口也叫“母亲”。次后与叔宝拜了四拜,一个叫“哥哥”,一个叫“兄弟”。末后拜了张氏,称“嫂嫂”;张氏也待如亲叔一般。
大凡人之精神血气,没有用处,便好的是生事打闹发泄;他有了用处,他心志都用在这里,这些强硬之气,都消了。人不遇制伏得的人,他便要狂逞;一撞着作家,竟如铁遇了炉,猢狲遇了花子,自然服他,凭他使唤。所以一个顽劣的罗士信,却变做了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叔宝教他枪法,日夕指点,学得精熟。
一日叔宝与士信正在场上比试武艺,见一个旗牌官,骑在马上,那马跑得浑身汗下,来问道:“这里可是秦家庄么?”叔宝道:“兄长问他怎么?”那旗牌道:“要访秦叔宝的。”叔宝道:“在下就是。”叫士信带马系了,请到茅堂。旗牌见礼过,便道:“奉海道大元帅来爷将令,赍有札符,请将军为前部先锋。”叔宝也不看,也不接,道:“卑末因老母年高多病,故隐居不仕,日事耕种,筋力懈弛,如何当得此任?”旗牌道:“先生不必推辞。这职衔好些人谋不来的。不要说立功封妻荫子,只到任散一散行粮路费,便是一个小富贵。先生不要辜负了来元帅美情,下官来意。”叔宝道:“实是母亲身病。”管待了旗牌便饭,又送了他二十两银子,自己写个手本,托旗牌善言方便。旗牌见他坚执,只得相辞上马而去。
原来来总管奉了敕旨,因想:“登莱至平壤,海道兼陆地,击贼拒敌,须得一个武勇绝伦的人。秦琼有万夫不当之勇,用他为前部,万无一失。”故差官来要请他。不意旗牌回复:“秦琼因老母患病,不能赴任,有禀帖呈上。”来总管接来看了道:“他总是为着母老,不肯就职。然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他不负亲,又岂肯负主?况且麾下急切没有一个似他的。”心中想一想道:“我有个道理。”发一个帖儿,对旗牌道:“我还差你到齐州张郡丞处投下,促追他上路罢。”这旗牌只得策马,又向齐州来,先到郡丞衙。
这郡丞姓张名须陀,是一个义胆忠肝,文武全备,又且爱民礼下的一个豪杰。当时郡丞看了帖儿,又问了旗牌来意。久知秦叔宝是个好男子,今见他不肯苟且功名,侥幸一官半职,“这人不惟有才,还自立品,我须自去走遭。”便叫备马,一径来到庄前。从人通报,郡丞走进草堂,叔宝因是本郡郡丞,不好见得,只推不在。张郡丞叫请老夫人相见。秦母只得出来,以通家礼见了,坐下。张郡丞开言道:“令郎原是将家之子,英雄了得。今国家有事,正宜建功立业,怎推托不往?”秦母道:“孩儿只因老身景入桑榆,他又身多疾病,故此不能从征。”张郡丞笑道:“夫人年虽高大,精神颇旺,不必恋恋。若说疾病,大丈夫死当马革裹尸,怎宛转床席,在儿女子手中?且夫人独不能为王陵母乎?夫人分付,令郎万无不从。明日下官再来劝驾。”说罢起身去了。
秦母对叔宝说:“难为张大人意思,汝只得去走遭。只愿天佑,早得成功,依然享夫妻母子之乐。”叔宝还有踌躇之意,罗士信道:“高丽之事,以哥哥才力,马到成功。若家中门户,嫂嫂自善主持。只虑盗贼生发,士信本意随哥哥前去,协力平辽;今不若留我在家,总有毛贼,料不敢来侵犯。”三人计议已定,次早叔宝又恐张郡丞到庄,不好意思,自己入城,换了公服,进衙相见。
张郡丞大喜,叫旗牌送上札符,与叔宝收了。张郡丞又取出两封礼来:一封是叔宝赆仪,一封是送秦老夫人菽水之资。叔宝不敢拂他的意,收了。叔宝谢别,张郡丞又执手叮咛道:“以兄之才,此去必然成功。但高丽兵诡而多诈,必分兵据守,沿海兵备,定然单弱。兄为前驱,可释辽水、鸭绿江勿攻。惟有浿水去平壤最近,乃高丽国都。可乘其不备,纵兵直捣。高丽若思内顾,首尾交击,弹丸之国,便可下了。”叔宝道:“妙论自当书绅。”就辞了出门。到家料理了一番,便束装同旗牌起行。罗士信送至一二里,大家叮咛珍重而别。
叔宝与旗牌日夕趱行,已至登州,进营参谒了来总管。来总管大喜,即拨水兵二万,青雀、黄龙船各一百号,俟左武卫将军周法尚,打听隋主出都,这边就发兵了。正是:
旗翻幔海威先壮,帆指平壤气已吞。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