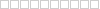第十六回 报德祠酬恩塑像 西明巷易服从夫
第十六回·西明巷易服从夫
诗曰:
侠士不矜功,仁人岂昧德。
置璧感负羁,范金酬少伯。
恩深自合肝胆镂,肯同世俗心悠悠。
君不见报德祠宇揭天起,报德酬恩类如此。
信陵君魏无忌,因妹夫平原君为秦国所围,亏如姬窃了兵符,与信陵君率兵十万,大破秦将蒙骜,救全赵国。他门客有人对信陵君道:“德有可忘者,有不可忘者:人有德于我,是不可忘;我有德于人,这不可不忘。”总之,施恩的断不可望报,受恩的断不可忘人。
话说王伯当乃弃隋的名公,眼空四海,他那里看得上那黄伞下的紫衣少年?齐国远、李如珪,青天白日放火杀人,那里怕那个打黄伞的尊官?秦叔宝却委身公门,知高识下,赶在甬道中间,将三友拦住道:“贤弟们不要上去,那黄伞底下坐的少年人,就是修寺的施主。”伯当道:“施主罢了,怎么就不走?”叔宝道:“不是这等说,是个现任的官员。”李如珪道:“兄怎么知道?”叔宝道:“用这两面虎头硬牌,想是现任官员。今我兄弟四人走上去,与他见礼好,还是不见礼好?”伯当道:“兄讲得有理。”四人齐走小甬道,至大雄宝殿,见许多的匠作,在那里做工。叔宝叫了一声,众人近前道:“老爷们有什么话分付?”叔宝道:“借问一声,这寺院是何人修建得这等齐整?”匠人道:“是并州太原府唐国公李老爷修盖的。”叔宝道:“他留守太原,怎么又到此间来干此功德?”匠人道:“因仁寿元年八月十五日,李老爷奉圣恩钦赐回乡,晚间寺内权住,窦夫人分娩了第二位世子,李爷怕秽污了清净地土,发心布施,重新修建。那殿上坐着打黄伞的,就是他的郡马,姓柴名绍,字嗣昌。”叔宝心中就知是那日在临潼山助他那一阵,晚间到此来了。
弟兄四人进东角门,就是方丈。见东边新起一座门楼,悬红牌书金字,写“报德祠”三字。伯当道:“我们看报什么德的。”四人齐进,见三间殿宇,居中一座神龛,高有丈余。里边塑了一尊神道,却是立身,戴一顶荷叶檐粉青色的范阳毡笠,着皂巾海衫,盖上黄罩甲,熟皮铤带,挂牙牌解刀,穿黄麂皮的战靴。向前竖一面红牌,楷书六个大金字:“恩公琼五生位。”旁边又是几个小字儿:“信官李渊沐手奉祀。”原来当年叔宝在临潼山打败假强盗时,李公问叔宝姓名,叔宝曰不敢通名,放马奔潼关道上。李公不舍,追赶十余里路,叔宝只得通名秦琼。李公见叔宝摇手,听了名,转不曾听姓,误书在此。叔宝暗暗点头:“那一年我在潞州,怎么颠沛到那样田地?原来是李老爷折得我这样嘴脸。我是个布衣,怎么当得勋卫塑像,焚香作念。”暗自感叹咨嗟。那三个人都看那像儿,齐国远连那六个金字都认不得,问:“伯当兄,这可是韦驮天尊么?”伯当笑道:“适才二山门里面朱红龛内,捧降魔杵,那便是韦驮。这个生位,其人还在,唐公曾受这人恩惠,故此建这个报德祠。”众人听见伯当说个“在”字,都惊诧起来。看看这个像,又瞧瞧叔宝的脸。那个神龛左右塑着四个人,左首二人,带一匹黄骠马。右首二人,捧两根金装锏。伯当近叔宝,附耳低言:“往年兄长出外远行,就是这等打扮?”叔宝暗暗摇首,叫:“贤弟低声,这就是我了。”伯当道:“怎么是兄?”叔宝道:“那仁寿元年,潞州相遇贤弟时,我与樊建威长安挂号出来,正是八月十五。唐公回乡,到临潼山被盗围杀,樊建威撺掇我向前助唐公一阵,打退强贼。那时我放马就走,唐公追赶来问我姓名。我没奈何,只得通名秦琼,摇手叫他不要赶,不知他怎么仓卒了,错记琼五,这话一些说不得。”伯当笑道:“只因他认你做琼将军,所以折得将军在潞州这样穷了。”两边说笑。不期那柴嗣昌坐在月台下,望见四人雄赳赳的进去,不知甚么人,分付家将暗暗打听。家将们就随在后边,看他举动。
叔宝们在祠堂内说话时,外面早有人听见,上月台来报郡马爷:“那四位老爷里面,有太老爷的恩人在内。”柴嗣昌听了,整衣下月台进报德祠,着地打一躬道:“哪位是妻父活命的恩公?”四人答礼,伯当指着叔宝道:“此兄就是李老大人临潼山相会的故人,姓秦名琼。李老大人当年仓卒,错记琼五。郡马如不信,双锏马匹现在在山门外面。”嗣昌道:“四位杰士,料不相欺,请到方丈。”命手下铺拜毡,顶礼相拜,各问姓名。齐国远、李如珪,都通了实在的姓名。郡马叫人山门外牵马,搬行李到僧房中打叠。就分付摆酒,接风洗尘。那夜就修书差人往太原,通报唐公。将他兄弟四人,款留寺内,饮酒作乐。
倏忽数日,又是新春,接连灯节相近。叔宝与伯当商议道:“来日向晚,就是正月十四,进长安还要收拾表章礼物,十五日绝早进礼。”伯当道:“也只是明日早行就罢了。”叔宝早晨分付健步收拾鞍马进城。柴嗣昌晓得他有公务,不好阻挠;只是太原的回书不到,心内踌蹰,暗想:“叔宝进长安,赍过了寿礼,径自回去了,决不肯重到寺中来。倘岳父有回书来敦请,此公去了,我前书岂不谬报?今我陪他进长安去,也就看看灯,完了他的公事,邀回寺来,好候我岳父回书。”嗣昌对叔宝道:“小生也要回长安观灯,陪恩公一行何如?”叔宝因搭班有些不妥当,也要借他势头进长安去,连声道好。嗣昌便分付手下收拾傢马,着众将督工修寺。命随身二人带毡包拜匣,多带些银钱,陪秦爷进京送礼。饭后起身,共是五俦英俊、七骑马、两名背包健步,从者二十二人,离永福寺进长安。叔宝等从到寺至今,才过半月,路上景色,又已一变:
柳含金粟拂征鞍,草吐青芽媚远滩。
春气着山萌秀色,和风沾水弄微澜。
虽是六十里路,起身迟了些,到长安时,日已沉西。叔宝留心,不进城中安下处,恐出入不便。离明德门还有八里路远,见一大姓人家,房屋高大,挂一个招牌,写“陶家店”。叔宝就道:“人多日晚,怕城中热闹,寻不出大店来,且在此歇下罢。”催趱行囊马匹进店,各人下马,到主人大厅上来,上边挂许多不曾点的珠灯。主人见众豪杰行李铺陈仆从,知是有势力的人,即忙笑脸殷勤道:“列位老爷不嫌菲肴薄酒,今晚就在小店,看了几盏粗灯,权为接风洗尘之意。到明日城中方才灯市整齐,进去畅观,岂不是好?”叔宝是个有意思的人,心中是有个主意:今日才十四,恐怕朋友们进城没事干,街坊玩耍,惹出事来。况他公干还未完,正好趁主人酒席,款留诸友。到五更天,赍过了寿礼,却得这个闲身子,陪他们看灯。叔宝见说,便道:“既承贤主人盛情,我们总酬就是了。”于是众友开怀痛饮,三更时尽欢而散,各归房安寝。
叔宝却不睡,立身庭前。主人督率手下收拾傢伙,见叔宝立在面前,问:“公贵衙门?”叔宝道:“山东行台来爷标下,奉官赍寿礼与杨爷上寿,正有一事奉求。”店主道:“甚么见教?”叔宝道:“长安经行几遍,街道衙门日间好认。如今我不等天明,要到明德门去,宝店可有识路的尊使,借一位去引路?”主人指着收傢伙一人道:“这个老仆名叫陶容,不要说路径,连礼貌称呼都是知道的。陶容过来!这位山东秦爷,要进明德门,往越府拜寿去,你可引路。”陶容道:“秦爷若带得人少,老汉还有个兄弟陶化,一发跟秦叔拿拿礼物。”叔宝道:“这个管家,果然来得。”回房中叫健步取两串皮钱,赏了陶容、陶化,就打开皮包,照单顺号,分做四个毡包。两名健步与陶容弟兄两个拿着,跟随在后。叔宝乘众友昏睡中,不与说知,竟出陶家店,进明德门去了不题。
却说越公乃朝廷元辅,文帝隆宠已极。当陈亡之时,将陈宫妃妾女官百员赐与越公为晚年娱景。越公虽是爵尊望重的大臣,也是一个奸雄汉子。一日因西堂丹桂齐开,治酒请幕僚饮宴。众人无不谀辞迎合,独李玄邃道:“明公齿爵俱尊,名震天下,所欠者惟老君丹一耳。”越公会意,即知玄邃道他后庭多宠,恐不能长久的意思,即便道:“老夫老君丹也不用,自有法以处之。”到明日越公出来,坐在内院,将内外锦屏大开,即叫人传旨与众姬妾道:“老爷念你们在此供奉日久,辛勤已著,恐怕误了你们青春。今老爷在后院中,着你们众姬妾出去。如众女子中有愿去择配者立左,不愿去者立右。”众女子见说,如开笼放鸟,群然蜂拥将出来,见越公端坐在后院。越公道:“我刚才叫人传谕你们,都知道了么?如今各出己见站定,我自有处。”众女子虽在府中受用,然每想单夫独妻,怎的快乐。准百女子,到有大半跪在左边。越公瞥转头来,只见还有两个美人:一个捧剑的是乐昌公主,陈主之妹;一个执拂的美人,是姓张名出尘,颜色过人,聪颖出众,是个义侠的奇女子。越公向他两个说道:“你二美人亦该下来,或左或右,也该有处。”二美人见说,走下来跪在面前。那个捧剑的涕泣不言,只有那执拂的独开言道:“老爷隆恩旷典,着众婢子出来择配,以了终身,也是千古奇逢,难得的快事。但婢子在府,耳目口鼻,皆是豪华受用,怎肯出去,与那瓮牖绳枢之子,举案终身?古人云:‘受恩深处便为家。’况婢子不但无家,视天下并无人。”越公见说,点头称善。又问捧剑的:“你何故只顾悲泣?”乐昌公主便将昔曾配徐德言、破镜分离之事,一一陈说。——后得徐德言为门下幕宾,夫妻再合,是后话。当时越公见说,也不嗟叹,便叫二美人起来站后,随分付总管领官,开了内宅门,叫那些站左的女子四五十人,俱令出外归家,自择夫婿。凡有衣饰私蓄,悉听取去。于是众女子各各感恩叩首,泣谢而出。越公见那些粉黛娇娥,拥挤出门,反觉心中爽快。自此将乐昌公主与执拂张氏,另眼眷宠,为女官,领左右两班金钗。
光阴荏苒。那年上元十五,又值越公寿诞。天下文武大小官员,无不赍礼上表,到府称贺。其时李靖恰在长安,闻知越公寿诞,即具揭上谒,欲献奇策。未到府门,官吏把揭拿去。此时越府尚未开门,只得走进侧首班房里伺候。那些差官将吏,亦俱在内忙乱。西边坐着一个虎背熊腰、仪表不凡的大汉,李靖定睛一看,便举手道:“兄是那里人氏?”那大汉亦起身举手道:“弟是山东人。”李靖道:“兄尊姓大名?”那人道:“弟姓秦名琼。”李靖道:“原来是历城叔宝兄。”叔宝道:“敢问兄长上姓何名?”李靖答道:“弟是三原李靖。”叔宝道:“就是药师兄?久仰!”两人重新叙礼,握手就坐,各问来因。叔宝问李靖所寓,靖答道:“寓在府前西明巷,第三家。”两人正在话得浓,忽听得府内奏乐开门,有一官吏进来喊道:“那个是三原李爷?老爷有旨请进去相见!”李靖对叔宝道:“弟此刻要进府去相见,不及奉陪;但弟有一要紧话,欲与兄说。兄欲不弃,千万到弟寓所细谈片晌。”叔宝唯唯。李靖即同那官儿进府。
越公本是尊荣得紧,文武官僚尚不轻见,缘何独见李靖?因李靖之父李受,生时与越公同仕于隋,靖乃通家子侄,久闻李靖之才名,故此愿见。其时那官儿引了李靖,不由仪门而走,乃从右手甬道中进去,到西厅院子内报名。李靖往上一望,见越公据胡床,戴七宝如意冠,披暗龙银裘褐,执如意。床后立着翡翠珠冠袍带女官十二员,以下群妾甚众,列为锦屏。李靖昂然向前揖道:“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当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越公敛容起谢,与靖寒温叙语,随问随答,娓娓无穷。越公大悦,欲留为记室,因是初会,未便即言。时有执拂美人,数目李靖。靖是个天挺英豪,怎比纨袴之子,见妇人注目偷视,就认做有顾盼小生之意,便想去调戏他?时已将午,李靖只得拜辞而出。越公曰通家子侄,即命执拂张美人送靖。张美人临轩对吏道:“主公问去者李生行第几,寓何处?可即他往否?”吏往外问明,进来回覆,张美人归内。
如今且慢题李靖回寓。再说秦叔宝押着礼物进越公府中,原来天下藩镇官将差遣赍礼官吏,俱分派在各幕僚处收礼。那些收礼的官,有许多难为人处:凡赍礼官员,除表章外,各具花名手本,将彼处土产礼物相送。稍不如意,这些收礼官苛刻起来,受许多的波查。那山东一路礼物,却派在李玄邃记室厅交收。是时秦琼到来,玄邃看见,慌忙降阶迎接,喜出意外。叔宝呈上表章礼仪,玄邃一览,叫人尽收。私礼尽璧,遂留叔宝到后轩取酒款待,细谈别后踪迹。叔宝把遇见王伯当同来的事,说了一遍。“但恐兄长事冗,不能出去一会。”并言:“遇见李靖,姿貌不凡,丰神卓荦。适才府门外相遇倾盖,如同夙契。小弟出去,就要到他寓所一叙。回书回批,乞兄作速打发。”玄邃见说,命青衣斟酒,自己却在案旁挥写回书回批,顷刻而就,付与叔宝。分手时,玄邃嘱托致意伯当,不得一面为恨。
叔宝别了玄邃,竟到西明巷来,李靖接见喜道:“兄真信人也。”坐定即问:“兄年齿多少?”叔宝道:“二十有四。”又问道:“兄入长安时,可有同伴否?”叔宝隐却下处四个朋友,便说:“奉本官差遣赍礼,止有健步两名,并无他人。兄长为何问及?”李靖道:“小弟身虽湖海飘蓬,凡诸子百家,九流异术,无不留心探讨,最喜的却是风鉴。兄今年正值印堂管事,眼下有些黑气侵人,怕有惊恐之灾,不敢不言。然他日必为国家股肱,每事还当爱鼎。小弟前日夜观乾象,正月十五三更时候,彗星过度,民间主有刀兵火盗之灾。兄长倘同朋友到京,切不可贪耍观灯游玩。既批回已有,不如速返山东为妙。”一番言语,说得叔宝毛骨耸然。念着齐国远在下处,恐怕惹出事来,慌忙谢别了李靖,要赶回下处。
今再说张美人,得了官吏回覆明白,进内自思道:“我张出尘在府中阅人多矣,未有如此子之少年英俊者,真人杰也。他日功名,断不在越公之下。刚才听他言语,已知他未有家室。想我在此奉侍,终非了局;若舍此人,而欲留心再访,天下更无其人。若此人不是我张出尘为配,恐彼终身亦难定偶。趁此今夜,非我该班,又兼府中演戏开宴之时,我私自到他寓所一会,岂不是好!”主意已定,把室中箱笼封锁,开一细账。又写一个禀帖,押在案上。又恐街上巡兵拦阻,转到内院去,把兵符窃了。改装做后堂官儿,提着一盏灯笼,大模大样走出府门。未有里许,见三四个巡兵问道:“爷是往那里去的?”张氏道:“我是越府大老爷有紧要公干,差往兵马司去的。你们问我则甚?”那巡兵道:“小的问一声儿何碍?”说罢,大家击梆鸣锣的去了。
不移时,已到府前西明巷口。张美人数着第三家,见有个大门楼,即便叩门。主人家出来开了,问:“是会那个爷的?”张氏道:“三原李爷,可是寓在此?”主人道:“进门东首那间房里。”张氏见说,忙走进来。其时李靖夜膳过,坐在房中灯下看那龙母所赠之书。只听见敲门,忙开门出来一看:
乌纱帽,翠眉束鬓光含貌。光含貌,紫袍软带,新装偏巧。 粉痕隐映樱桃小,兵符手握殷勤道。殷勤道,疑城难破,令人思杳。
张美人走进,将兵符供在桌上,便与李靖叙礼坐定。李靖问道:“足下何处来的?到此何干?”张氏道:“小弟是越府中的内官姓张,奉敝主之命差来。”李靖道:“有甚见教?”张氏道:“适间敝主传弟进去,当面嘱付许多话,如今且慢说。先生是识见高广、颖悟非常的人,试猜一猜。若是猜得着,乃见先生是奇男子,真豪杰。”李靖见说:“这又奇了,怎么要弟猜起来?”低头一想,便道:“弟日间到府拜公之时,承他屈尊优待,殷勤款洽,莫非要弟为其入幕之宾否?”张氏道:“敝府虽簿书繁冗,然幕僚共有一二十人,皆是多材多艺之士,身任其责。不要说敝主不敢有屈高才,设有此意,先生断不肯在杨府作幕。请再猜之。”李靖道:“这个不是。莫非越公要弟往他处作一说客,为国家未雨绸缪之意?”张氏道:“非也,实对先生说了罢。越公有一继女,才貌双绝,年纪及笄,越公爱之,不啻己出。今见先生是个英奇卓荦,思天下佳婿未有如先生者,故传旨与弟,欲弟与先生为氤氲使耳。”李靖见说道:“这那里说起!弟一身四海为家,迹同萍梗;况所志未遂,何暇议及室家之事?虽承越公高谊,然门楣不敌,尊卑有亵,此事断乎不可!烦兄为我婉言辞之。”张氏道:“先生何其迂也!敝主乃皇家重臣,一言之间,能使人荣辱。倘若先生赘入豪门,将来富贵,正未可量,何乃守经而遽绝之?先生还宜三思。”李靖道:“富贵人所自有,姻缘亦断非逆旅论及,容以异日。如再相逼,弟即此刻起身,浪游齐楚间矣!”张氏正容道:“先生不要把这事看轻了。倘弟归府,将尊意述之,设敝主一时震怒,先生虽有双翅,亦不能飞出长安,那时就有性命之忧了。”李靖变了颜色,立起身来道:“你这官儿好不恼人!我李靖岂是怕人的?随你声高势重,我视之如同傀儡。此事头可断,决不敢从!”
两人正在房里嚷乱,只听见间壁寓的一人,推门进来,是武卫打扮,问道:“那位是药师兄?”李靖此时气得呆了,随口应道:“小弟便是。”张氏注目,把那人一看,忙举手道:“尊兄上姓?”那人道:“我姓张。”张氏道:“妾亦……”说了两个字,缩住了,忙改口道:“这小弟亦姓张,如若不弃,愿为昆仲。”那人见说,复仔细一认,哈哈大笑道:“你要与我结弟兄甚妙。”那时李靖方问道:“张兄尊字?”那人道:“我字仲坚。”李靖上前执手道:“莫非虬髯公么?”那人道:“然也。我刚才下寓在间壁,听见你们谈论,知是药师兄,故此走来。前言我已听得。但此位贤弟,并不是为兄执柯者。细详张贤弟的心事,莫若爽利待弟说了出来,到与二位执柯何如?”张氏道:“我的行藏,既是张兄识破,我也不便隐瞒了。”走去把房门闩上,即把乌纱除下,卸去官裳,便道:“妾乃越府中女子。因见李爷眉宇不凡,愿托终身,不以自荐为丑,故尔乘夜来奔。”仲坚见说大笑称快。李靖道:“莫非就是日间执拂的美人么?既贤卿有此美意,何不早早明言,免我许多回肠。”张氏道:“郎君法眼不精,若我张哥,早已认出,不烦贱妾饶舌了。”仲坚笑道:“你夫妇原非等闲之人,快快拜谢了天地!待我去取现成酒肴来,权当花烛,畅饮了三杯,何如?”两人见说,欣然对天拜谢了。
张氏复把官裳穿好,戴上乌纱。李靖道:“贤卿为何还要这等装束?”张氏道:“刚才进店来,是差官打扮;今若见我是个妇人,反有许多不妥了。”李靖忖道:“好一个精细女子。”仲坚教手下移了酒肴进来,大家举杯畅谈。酒过三杯,张氏问仲坚道:“大哥几时起身?”仲坚道:“心事已完,明日就走。”张氏见说,立起身来道:“李郎陪我张哥畅饮,我到一个所在去,如飞的就来。”李靖道:“这又奇了,还要到那里去?”张氏道:“郎君不必猜疑,少刻便知分晓。”说完点灯竟出房门。李靖见此光景,老大狐疑。仲坚道:“此女子行止非常,亦人中龙虎,少顷必来。”两人又说了些心事。只听得门外马嘶声响,张氏早已走到面前。仲坚道:“贤妹又往何处去了来?”张氏道:“妾逢李郎,终身有托,原非贪男女之欲。今夜趁此兵符在手,刚才到中军厅里去讨了三匹好马。我们吃完了酒,大家收拾上马出门。料有兵符在此,城门上亦不敢拦阻,即借此脚力,以游太原,岂非两便!”两人见说,称奇赞叹。吃完了酒,即便收拾行装,谢别主人,三人上马,长扬的去了。
越公到明日,因不见张美人进内来伺候,即差人查看。来回复道:“房门封锁,人影俱无。”越公猛省道:“我失检点,此女必归李靖矣!”叫人开了房门,室中衣饰细软,纤毫不动,开载明白,同一禀帖留于案上。取来呈上越公,上写道:
越国府红拂侍儿张出尘,叩首上禀:妾以蒲柳贱质,得傍华桐,虽不及金屋阿娇,亦可作玉盘小秀,有何不满,遽起离心?妾缘幼授许君之术,暂施慧眼,聊识英雄,所谓弱草依兰,嫩萝附竹而已。敢为张耳之妻,庸奴其夫哉!临去朗然,不学儿女淫奔之态。谨禀。
越公看罢,心中了然。又晓得李靖也是个英雄,戒谕下人不许声扬,把这事就丢开不提。
但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