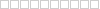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真知,以精审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真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蔽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真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哽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分类:答顾东桥书
【原文】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①。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②,小杖、大杖③,割股④、庐墓⑤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⑥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真知,以精审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真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蔽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真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哽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⑦,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注释】
①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语出《中庸》“君子之道费而稳。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②养志、养口:典出《孟子·离娄上》。
③小杖、大杖:典出《孔子家语·六本》。曾子在瓜地锄草时,锄掉了瓜苗。其父大怒,用大杖将其打昏在地。曾子醒来后,先向父亲请安,又回到屋里弹琴,使父亲知道自己安然无恙。孔子知道后很生气,教育曾子应像大舜侍奉父亲那样,父亲用小杖打时则坦然承受,用大杖打时就逃跑,以免使自己身体受伤,使父亲背上不义的罪名。
④割股: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流亡时,介子推曾割大腿上的肉给文公吃。后以割股治疗父母之病为至孝。
⑤庐墓:古时,父母亡故后,孝子在墓旁搭建草棚,一般要住三年,以表达对父母的哀思怀念之情。
⑥“道在迩”二句:语出《孟子·离娄上》。
⑦为无后:语出《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翻译】
你来信写道:“圣道的宗旨很容易明白,就像先生说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具体的细节,随着时间的变化,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需要学习之后才能明白。谈论孝道就是温凊定省这些礼节,现在谁不明白?至于舜不请示父母就娶妻,武王还没有安葬文王便兴师伐纣,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割股疗亲,为亲人守墓三年等事情,可能正常,可能不正常,这是处于过分与不足之间。必须讨论个是非曲直,作为处事的原则。然后人的心体没有遮蔽,这样临事才能没有过失。”
“圣道的宗旨很容易明白”,这句话是对的。只是后世的学者们往往忽略那些简单明白的道理不去遵循,却去追求那些很难明白的东西,这正是“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孟子说:“圣道像大路一样,难道很难明白吗?人们的毛病在于不去遵循罢了。”愚夫愚妇和圣人是同样拥有良知良能的。只是圣人能够意识并保存自己的良知,而愚夫愚妇则不能,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节目时变”,圣人对此岂有不知的?只是不一味地在这上面做文章罢了。圣人的学问,与后世所说的学问不同,它只是意识并保存自己的良知,以精确体察心中的天理。你不去保存自己的良知,而是念念不忘这些细节,这正是将那些难于理解的东西当作学问的弊病了。良知对于随着时间变化的具体细节,就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方圆长短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具体细节随时间变化也不能够事先预测。因此,规矩尺度一旦确立,那么方圆长短就能够一目了然了,而天下的方圆长短也就用不完了。确实已经达到了致良知的境界,那么具体细节随时间的变化也就一览无余,天下不断变化的细节就能应付自如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在我们本心的良知上的细微处去体察,那你怎么去应用你所学的东西呢?这是不依照规矩尺度想去确定天下的方圆长短。这种狂妄的说法,只会每天徒劳而一无所成。
你说“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真正知道的人很少。如果说简单地知道一些温凊定省的礼节,便能认为他已经做到了致孝的良知。那么凡是那些知道应当仁爱百姓的国君,都能认为他能够致仁爱的良知;凡是知道应当忠诚的臣子,都能认为他能致忠诚的良知,那么天下哪个不是能够致良知的人呢?由此便明显可见,“致知”必须实践,没有实践便不能够称他能够“致知”。这样知行合一的概念,不是更加清楚了吗?
舜不告知父母而娶妻,难道是在舜之前便已经有了不告而娶的准则,所以舜能够考证某部经典或者询问于某人才这样做的吗?还是他依照心中的良知,权衡利弊轻重,不得已才这样做?周武王没有安葬文王便兴师伐纣,难道是武王之前便已经有了不葬而兴师的准则,所以武王能够考证某部经典或者询问某人才这样做的吗?抑或是他依照自己心中的良知,权衡利弊,不得已才这样做?如果舜并非担心没有后代,武王并非急于拯救百姓,那么,舜不禀报父母而娶妻,武王不葬文王而兴师,便是最大的不孝和不忠。后世的人不努力致其良知,不在处理事情上精细地体察天理,只顾空口谈论这中间时常变化的事物,并执着于此作为处理事情的准则,以求得遇事时没有过失,这也差得太远了。其余几件事也能够依此类推,那么古人致良知的学问就可以明白了。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