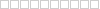来书云:“所释《大学》古本,谓致其本体之知,此固孟子尽心之旨。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然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则其所以为是语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若鄙人之见,则与朱子正相反矣。未“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岂可专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乎?吾子骤闻此言,必又以为大骇矣。然其间实无可疑者,一为吾子言之。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此惟圣人而后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尽其心者也,故须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于存而自无不存,然后可以进而言尽。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天为二也。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养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也。故曰: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至于“夭寿不贰”,则与存其心者又有间矣。存其心者虽未能尽其心,固已一心于为善,时有不存则存之而已。今使之“夭寿不贰”,是犹以夭寿二其心者也。犹以夭寿二其心,是其为善之心犹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尽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寿二其为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寿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于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己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则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犹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创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尝有而今始建立之谓,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使初学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责之以圣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风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几何而不至于“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见矣。吾子所谓“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者,无乃亦是过欤?此学问最紧要处,于此而差,将无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于罪戮,呶呶其言,其不容己者也。
分类:答顾东桥书
【原文】
来书云:“所释《大学》古本,谓致其本体之知,此固孟子尽心之旨。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①。然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则其所以为是语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若鄙人之见,则与朱子正相反矣。未“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岂可专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乎?吾子骤闻此言,必又以为大骇矣。然其间实无可疑者,一为吾子言之。
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此惟圣人而后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尽其心者也,故须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于存而自无不存,然后可以进而言尽。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天为二也。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养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②者也。故曰: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至于“夭寿不贰”,则与存其心者又有间矣。存其心者虽未能尽其心,固已一心于为善,时有不存则存之而已。今使之“夭寿不贰”,是犹以夭寿二其心者也。犹以夭寿二其心,是其为善之心犹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尽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寿二其为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寿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于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己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则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犹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创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③。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尝有而今始建立之谓,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
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使初学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责之以圣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风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几何而不至于“率天下而路④”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见矣。吾子所谓“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者,无乃亦是过欤?此学问最紧要处,于此而差,将无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于罪戮,呶呶其言,其不容己者也。
【注释】
①“朱子”句:语出《中庸章句序》“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
②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语出《礼记·祭仪》“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意为父母把子女完好地生下来,子女要好好地保全身体发肤,等到死时完完整整地归还给父母,这才是孝。
③“立德”句: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讲做人的几种境界。
④率天下而路:语出《孟子·滕文公上》“且一人之身,而百功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意为对一个人来说,各种工匠的产品对他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每件东西都要自己制造出来才能用,这是率领天下的人疲于奔命。
【翻译】
你来信说:“先生注释的《大学》旧本提到对心的本体的认识是致知,孟子‘尽心’的宗旨与此是相同的。而朱熹先生也用虚灵知觉当作是心的本体。但是因为认识的天性才会尽心,致知要依靠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这话是正确的。但是我看你说这话,大概是因为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朱熹先生把“尽心、知性、知天”当作是格物、致知,把“存心、养性、事天”当作是诚意、正心、修身,而把“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当作是认识的最高境界、仁爱的顶峰,是圣人做的事。但在我看来,正好相反了。“尽心、知性、知天”,即所谓的天生就知道,天生就能够实践,是圣人才能够做得到的;而“存心、养性、事天”,学习就能够知道,并且顺利实践,是贤人能够做到的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获得知识很艰难,实践起来也很勉强,便是学者们的事。怎么能简单地把“尽心知性”当作为识,而把“存心养性”当作行呢?你听到我这话,一定又会为此非常惊奇了。然而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我一一给你解释。
心的本体就是性;人的本原就是理。能尽其心,就是能够尽其天性。《中庸》中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天性。”又说:“知道万物的生化孕育,崇拜鬼神,而没有产生疑问,这是知天。”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些,所以我说:圣人才能做到先生就知道和实践。存养本心,说明还不能够做到尽心,还必须加上个存养的功夫;存养心性很久之后,到了不需要特地去存养而时刻都在存养的境界,才能进一步到达尽心的境界。“知天”中的“知”,就像“知州”“知府”中的“知”意思一样,知州、知县把管理一州、一县当作是自己的事情,“知天”,就是与天合而为一体。“事天”则像儿子孝顺父亲,大臣侍奉君王,还没有达到与天合而为一的地步。上天给予我们的,是心、是性,我们只需存起它而不丢失,修养它不损害,就像“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一样。所以我说:这种“学知利行”,是贤人做的事。至于“夭寿不贰”,则和存养本心的人又还有些差距。存养本心的人虽然没有尽心,但本来就已经是一心为善,失去了本心的时候再存养它就行了。现今要求人不论夭寿始终如一,这依然是将夭寿一分为二。仍旧将夭寿一分为二,因为寿命的长短而分心,是因为他为善之心还不能始终如一,尚且不可能存养它,尽心更从何说起呢?现在暂且让人们不再因为生命的长短而改变向善的心,好比说生死夭寿都有定数,我们只需一心向善,修养我的身心来等待天命的安排,主要是因为他平日还不知道有天命呢。事天虽然是将天与人分而为二,但已经知道恭恭敬敬地去承受天命了。那些等待天命降临的人,是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天命存在于何处,仍旧只是在等待天命,所以孟子说:“所以立命。”“立”,即“创立”的“立”,就像“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中的“立”。凡是说到“立”,都是指以前从未有过而如今开始建立的意思,也就是孔子所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的人。所以说:这种“困知勉行”,属于学者的事情。
现在把“尽心、知性、知天”当作格物、致知,当初学者尚不能做到一心一意时,就拿他不能像圣人那样天生就认识和实践来指责,这简直是无中生有,让人摸不着头脑,使得人们疲于奔命。如今世上格物、致知的弊病已经明显可见了。你说注重外在的学习,而忽略掉内心的存养,博学但又没有学到要领,这不也是它的弊病之一吗?在做学问最关键的地方出了差错,就会无处不出差错了。这也是我之所以冒着天下人的否定、嘲笑,不顾身陷罗网,仍喋喋不休的原因。

元芳,你怎么看?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